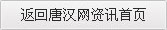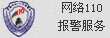《本草新编》卷之二商集
卷之二商集
天门冬天门冬,味苦而甘,性凉,沉也,阴(一本作"降")也,阴中有阳,无毒。入肺、肾二经。补虚痨,杀虫,润五脏,悦颜色。
专消烦除热,止嗽定咳尤善,止血消肺痈有神。但性凉,多服颇损胃。世人谓天门冬善消虚热,吾以为此说不可不辨。天门冬止可泻实火之人也,虚寒最忌,而虚热 亦宜忌之。盖虚热未有不胃虚者也。胃虚而又加损胃之药,胃气有不消亡者乎。胃伤而传之脾,则脾亦受伤。脾胃两伤,上不能受水谷,而下不能化糟粕矣,又何望 其补哉。大约天冬,凡肾水亏而肾火炎上者,可权用之以解氛,肾大寒而肾水又弱者。断不可久用之以滋阴也。
或谓天之冬性润,可以解火,即可以益水,先生谓不可久用者,以肾火之寒也,但肾火寒者,自不可用矣,肾水未竭,而肾火未寒者,亦可用之乎。此则愚所未言 也。肾水未竭,而肾火未寒者,是平常无病之人也。似乎服天冬,可以无碍。然而补之药胜于天冬者甚多,何必择此性凉者,以日伐其火乎。夫人非水火不生活,且 水非火不生,火非水不养。
止补其水而泻其火,初则火渐衰而水旺,久则火日去而水亡。此天冬所以止可暂以补水,而不可久以泻火也。
或问:天冬同地黄用之,可以乌须发,此久治之法以滋肾者,而吾子谓天冬止宜实火之人,岂乌须发而亦可谓实火耶?夫须发之早白,虽由于肾水之不足,亦因于肾 水之有余也。夫火之有余,既因于水之不足,刚寒凉以补水,正寒凉以泻火也。况天冬与地黄同用,则天冬之凉者不凉,肾得其滋补之益,而须发之焦枯,有不反黑 者哉。然则天冬之乌须发,仍泻实火,而非泻虚火矣。
或问:天门冬治痨瘵之病甚佳,而吾子谓止可暂服,岂治痨疾者,可一二剂愈乎?嗟乎。天门冬治痨瘵者,必脾健而大肠燥结、肺气火炎者宜之。然亦止可少服,而 不可多服也。夫寒凉之物,未有不损胃者也。脾健则胃气亦健。大肠燥结、则肺气亦必燥结。天冬凉肺而兼凉胃,宜其无恶,但久用天冬,胃凉则脾亦凉,肺凉则大 肠亦凉,又势所必至也,乌可不先事而预防哉。
或问:湿热不去,下流于肾,能使骨痿。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天门冬、黄柏之类是也。是天门冬味苦气寒,正入肾以除热,可以治痿,而竟置不言,何也?此吾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治痿必治阳 明。骨痿虽属肾,而治法必兼治胃。天门冬大寒,不利胃气,暂服可以治痿,久服必至损胃,胃损而肾又何益耶。况胃又肾之关门,关门无生气之固,而欲肾宫坚 牢,以壮骨生髓,必不得之数也。世人遵黄柏、知母之教,以损伤胃气。铎又何敢复扬天门冬治痿之说,以劝人再用寒凉乎。此所以宁缺,以志予过也。
或疑天冬泻实火,不泻虚火,虚火禁用,实火安在不可常用耶?夫火虽有虚、实之分。
而泻火之药,止可暂用,而不可常用也。天门冬泻实火,未尝不佳,特怪世人久服耳。人非火不活,哲损其有余,使火不烁水已耳,乌可经年累月服泻火之药哉。泻之日久,未有实火而不变为虚火者也。此常服之断宜戒也。
或疑天门冬性虽寒,以沙糖、蜜水煮透,全无苦味,则寒性尽失,不识有益阴虚火动之病乎?夫天门冬之退阴火,正取其味苦涩也。
若将苦涩之味尽去,亦复何益。或虑其过寒。
少去其苦涩,而加入细节甘草,同糖、蜜共制,庶以之治阴虚咳嗽,两有所宜耳。
或问:天门冬,古人有服而得仙,吾子贬其功用,谓多服必至损胃,然则古语荒唐乎?嗟乎!《神农本草》服食多载长生,岂皆不可信乎?大约言长生者,言其能延 生也,非即言不死也。天门冬,食之而能却病,吾实信之,谓采服飞升,尚在阙疑。麦门冬麦门冬,味甘,气微寒,降也,阳中微阴,无毒。人手太阴、少阴。泻肺 中之伏火,清胃中之热邪,补心气之劳伤,止血家之呕吐,益精强阴,解烦止渴,美颜色,悦肌肤。退虚热神效,解肺燥殊验,定嗽咳大有奇功。真可恃之为君,而 又可藉之为臣使也。但世人未知麦冬之妙,往往少用之而不能成功,为可惜也。不知麦冬必须多用,力量始大。盖火伏于肺中,烁干内液,不用麦冬之多,则火不能 制矣。热炽于胃中,熬尽真阴,不用麦冬之多,则火不能息矣。夫肺为肾之母,肺燥则肾益燥,肾燥则大小肠尽燥矣。人见大小肠之干燥,用润肠之药。然肠滑而脾 气愈虚,则伤阴而肾愈虚矣。肾虚必取给于肺金。而肺又素燥,元气以滋肾,而干咳嗽之症起,欲以些小之剂益肺气以生肾水,必不得之数也。抑肺又胃之子也,胃 热则土亏,土亏而火愈炽。
火炽,必须以水济之,而胃火太盛,肾水细微,不特不能制火。而且熬干津液。苟不以汪洋之水,速为救援,水立尽矣。然而大旱枯涸,滂沱之水,既不可骤得。倘 肾水有源,尚不至细流之尽断,虽外火焚烁,而渊泉有本,犹能浸润,不至死亡也。故胃火之盛,必须补水,而补水之源,在于补肺。然而外火既盛,非杯水可解。 阴寒之气,断须深秋白露之时,金气大旺,而后湛露湑湑,多且浓也。故欲肺气之旺,必用麦冬之重。苟亦以些小之剂,益其肺气,欲清胃火之沸腾也,又安可得 哉。更有议者,肝木畏肺金之克者也。然肺过于弱,则金且不能克木,而肝且欺之。于是,木旺而挟心火以刑金,全不畏肺金之克。肺欲求救肾子,而肾水又衰,自 顾不遑,又安能顾肺金之母哉。乃咳嗽胀满之病生,气喘痰塞之疾作。
人以为肺之病也,用泻肺之药,益虚其肺气,而肝木更炽,心火愈刑.,病有终年累月而不痊者。苟不用麦冬大补肺气,肝木之旺,何日能衰乎。此麦冬之必须多用,又不可不知也。
更有膀胱之火,上逆于心胸,小便点滴不能出。人以为小便大闭,由于膀胱之热也,用通水之药不效,用降火之剂不效,此又何故乎?盖膀胱之气,必得上焦清肃之 令行,而火乃下降,而水乃下通。夫上焦清肃之令,禀于肺也,肺气热,则清肃之令不行,而膀胱火闭,水亦闭矣。故欲通膀胱者,必须清肺金之气。
清肺之药甚多,皆有损无益,终不若麦冬清中有补,能泻膀胱之火,而又不损膀胱之气,然而少用之,亦不能成功。盖麦冬气味平寒,必多用之,而始有济也。
或问:麦冬以安肺气,救肺即可生肾子矣,何以补肺者,仍须补肾乎?曰:肺肾之气,未尝不两相须也。肺之气,夜必归于肾,肾之气,昼必升于肺。麦冬安肺,则肺气可交于肾,而肾无所补,则肾仍来取给于肺母,而肺仍不安矣。此所以补肺母者,必须补肾子也。
肾水一足,不取济于肺金之气,则肺气自安,且能生水,而肺更安也。麦冬止可益肺,不能益肾。古人所以用麦冬必加入五味子,非取其敛肺,正取其补肾也。
或问:麦冬加五味以补肾,敬闻命矣,何孙真人加入人参为生脉散?吾子善辨,幸明以教我。此则子不下问,而铎亦急欲阐明之也。夫肺主气也,人参补气,汤名补 气,谁日不然。而孙真人不言生气而言生脉者,原有秘旨。心主脉,是生脉者,生心之谓也。或疑心主火,而肺主金,生心火,必至克肺金矣。
益气之谓何?而讵知心之子,乃胃土也。肺金非胃土不生,胃弱以致肺金之弱。补心火。
自生胃土矣,胃土一生,而肺金之气自旺。又恐补心以克肺金,加麦冬以清肺,则肺不畏火之炎,加五味以补肾,则肾能制火之盛,调和制伏之妙,为千古生人之法,示天下以补心之妙,不必畏心之刑金也。所以不言生气而日生脉者,其意微矣,人未之思尔。
或问:麦冬补肺金而安肺气,肺气之耗者,宜加用麦冬以补肺金矣,然而日用麦冬,而不见肺金之气旺者,何故?盖肺金之母胃土之衰也。胃喜温而不喜寒,日用麦 冬之寒以益肺,而反致损胃,胃寒而气不能生金,徒用麦冬何益哉。必须用温胃之药,以生胃气,而后佐之以麦冬,则子母两朴,自然胃气安,而肺气亦安也。
或疑胃中有火,最宜麦冬以清之,而吾子日胃喜温不喜寒,不相反耶?非反也。胃乃土也,土自喜温。胃中宜火,何以恶火?夫火多宜泻,而火少宜补,况胃中之火 乃邪火。非正火也。邪火宜泻,而正火亦宜补。服麦冬而胃寒者,乃正火衰微,自宜补之,未可以胃中之正火,错认作邪火而并观也。
或问:麦冬滋肺气者也,何以有时愈用而愈不效,岂麦冬非滋肺药乎?夫麦冬不滋肺气,又何药以滋肺。然用之不效者,非麦冬不滋肺气,乃肺绝不受麦冬之滋也。 肺为娇脏,治肺原不宜直补肺也。肺至麦冬之不可滋者,脾胃之母气、肾经之子气,已先绝于肺之前,而欲用麦冬以救肺绝之际,又何可得哉。
或疑用麦冬以救肺气,肺绝而不可救,是麦冬为无用矣。不识舍麦冬,又用何药可救耶?曰:脾胃已绝,金不能生矣;肾经已绝,金无以养矣,实无药可以相救。惟 胃气不绝者,尚有可救之机,仍用麦冬为君。加于人参、熟地、山药、山茱萸之内,尚可延留一线。然不节欲慎疾,亦徒然也。
或问:麦冬乃肺经之药,凡肺病固宜用之,不识于治肺之外,尚有何症宜用也?夫麦冬不止治肺也,胃火用之可降,肾水用之可生,心火用之可息,肝木用之可养。胆木用之可滋,心包火用之可旺,三焦火用之可安,膀胱水用之可泻,所治之病甚多,何独于治肺耶。
或问:麦冬但闻可以内治成功,未知亦可以治外症乎?曰:麦冬之功效,实于内治独神,然又能外治汤火,世人固不识也。凡遇热汤滚水泡烂皮肉,疼痛呼号者,用麦冬半斤,煮汁二碗,用鹅翎扫之,随扫随干,随干随扫,少顷即止痛生肌,神效之极,谁谓麦冬无外治哉。
五味子五味子,昧酸,气温,降也。阴中微阳,非阳中微阴也。元毒。此药有南北之分,必以北者为佳,南者不可用。古人为南北各有所长,误也。最能添益肾水,滋补肺金,尤善润燥,非特收敛肺气。盖五味子人肺、肾二经,生津止渴,强阴益阳,生气除热,止泻痢有神。
但不宜多用,多用反无功,少用最有效。尤不宜独用,独用不特无功,且有大害。必须同补药用人汤丸之内,则调和无碍,相得益彰耳。
或问:五味子乃收敛之药,用之生脉散中,可以防暑,岂北五味亦能消暑耶?曰:五味子,非消暑药也。凡人当夏热之时,真气必散,故易中暑。生脉,用人参以益 气,气足则暑不能犯;用麦冬以清肺,肺清则署不能侵;又佐之北五昧,以收敛其耗散之金。则肺气更旺,何惧外署之热。是五味子助人参、麦冬以生肺气,而非辅 人参、麦冬以消暑邪也。
或问:五味子补肾之药,人皆用之于补肺,而吾子又言宜少用,而不宜多用,不愈示人以补肺。而不补肾乎?曰:北五味子补肾,正不必多也,其味酸而气温,味酸则过于收敛,气温则易动龙雷,不若少用之,反易生津液,而无强阳之失也。
或问:五味子,古人有独用以闭精,而吾子谓不宜独用,不独无功,且有大害,未知所谓大害者,何害也?夫五味子性善收敛,独用之者,利其闭精而不泄耳。精宜 安静,不宜浮动。服五味子而能绝欲者,世无其人,保其遇色而不心动乎。心动,则精必离宫,无五味子之酸收,则精将随小便而暗泄。惟其不能不心动也,且有恃 五味子之闭涩,搏久战以贪欢,精不泄而内败,变为痈疽发背而死者,多矣。所谓大害者如此,而可独用一味,经年累月知服,以图闭涩哉。
或问:五味子滋不足之肾水,宜多用为佳,乃古人往往少用,岂能生汪洋之肾水耶?曰:天一生水,原有化生之妙,不在药味之多也。孙真人生脉散,虽名为益肺, 其实全在生肾水。盖补肾以生肾水,难为力,补肺以生肾水,易为功。五味子助人参,以收耗散之肺金,则金气坚凝,水源渊彻,自然肺足而肾亦足也。又何必多用 五味子始能生水哉,况五味子多用,反不能生水,何也?味酸故也。酸能生津,而过酸则收敛多,而生发之气少,转夺人参之权,不能生气于无何有之乡,即不能生 精于无何有之宫矣。此古人所以少用,胜于多用也。
或问:北五味补肾益肺,然有时补肾而不利于肺,或补肺而不利于肾,何也?曰:肾乃肺之子,肺乃肾之母,补肺宜益于肾,补肾宜益于肺。何以有时而不利耶?此 邪火之作祟。补肾,则水升以入肺,而肺且恃子之水,与邪相斗,而肺愈不安矣。益肺,则金刚以克肝,而肝且恃母之水,与邪相争,而肾亦不安矣。然则五味子之 补肾益肺,宜于无邪之时,而补之益之也。
或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未必非五味子之味也。嗟乎,何子言之妙也,实泄天地之奇。精不足者宜补,五味之补也。世人见五味子不可多用,并疑五味子不能生 水。谁知此物补水,妙在不必多也。古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人参、羊肉是也。谁知人参、五味子之更胜哉?或问:五味子生精敛气之外,更有何病可以兼治之 乎?五味子敛耗散之肺金,滋涸竭之肾水,二治之外,原无多治法也。然子既求功于二者之外,我尚有一法以广其功。五味子炒焦,研末,敷疮疡溃烂,皮肉欲脱 者,可保全如故,不至全脱也。
菟丝子.菟丝子,昧辛、甘,气温,无毒。人心、肝、肾三经之药。益气强阴,补髓添精,止腰膝疼痛,安心定魂,能断梦遗,坚强筋骨,且善明日。可以重用,亦可一味专用,世人未知也。
余表而出之。遇心虚之人,日夜梦精频泄者,用菟丝子三两,水十碗,煮汁三碗,分三服,早、午、夜各一服即止,且永不再遗。其故何也?盖梦遗之病,多起于淫 邪之思想,思想未已,必致自泄其精,精泄之后,再加思想,则心火暗烁,相火乘心之虚,上夺君权,火欲动而水亦动矣,久则结成梦想而精遗。于是,玉关不闭, 不必梦而亦遗矣。此乃心、肝、肾三经齐病,水火两虚所致。菟丝子正补心肝肾之圣药,况又不杂之别味,则力尤专,所以能直入三经以收全效也。他如夜梦不安, 两目错暗,双足乏力,皆可用至一二两。同人参、熟地、白术、山茱之类用之,多建奇功。古人云:能断思交,则不尽然也。
或问:菟丝可多用以成功,何千古无人表出,直待吾子而后未奇乎?曰:轩岐之秘,不传于世也久矣。吾躬受岐夫子真传而秘之,则是轩岐之道,自我而传,亦自我而绝矣。故铎宁传之天下,使当世怀疑而不敢用,断不可不传之天下,使万世隐晦而不知用也。
或疑菟丝子元根之草,依树木而生,其治病,亦宜依他药而成功,似未可专用也。噫,何论之奇也。夫菟丝子,神药也,天下有无根草木如菟丝子者乎,亡有也。故 其治病,有不可思议之奇。人身梦遗之病,亦奇病也。无端而结想,无端而入梦,亦有不可思议之奇。虽《灵枢经》有"淫邪发梦"之篇,备言梦症。而终不得其所 以入梦之故。虽圣人,亦难言也。
用菟丝子治梦遗者,以异草治异梦也,乃服之而效验如响,亦有不可思议之奇,吾不意天地间之多奇如此。虽然菟丝治梦遗者何足奇,奇在吾子之发论,余得共阐其奇耳。惟其奇,故菟丝专用以出奇,又胡必依草木共治而后成功哉。
或问:菟丝子治梦遗,奇矣,亦可更治他病,能收奇功乎?夫菟丝子,实不止治梦遗也,更能强阳不倒。用一味至二两,煎汤服,则阳坚而不泄矣。或人不信吾方之奇。不知菟丝子,实神药也,以神通神,实有至理。凡人人房而易泄者,以心君之神先怯耳。心之神怯,则相之神旺矣。相之神旺,则阳易举。
亦易倒。心之神旺,则相之神严肃.而不敢犯君,则君之权尊。君之权尊.则令专而不可摇动,故阳不举则已,举则坚而不易倒也。菟丝子,能安心君之神,更能补 益心包络之气,是君火与相火同补,阳安有不强者乎。况菟丝子更善补精髓,助阳之旺,又不损阴之衰,此强阳不倒之可以无虞,而不至有阴虚火动之失也。虽然铎 创此论,宣菟丝子神奇,非导淫也。倘阳火衰徼,服此方,可以获益而种子。
设或阴虚火盛,服此方,必有虚阳亢炎之祸,至痨瘵而不可救者,非铎之过也。
甘菊花甘菊花,味甘、微苦。性徽索,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无毒。人胃、肝二经。能除大热,止头痛晕眩,收眼泪翳膜,明日有神,黑须鬓颇验,亦散湿去瘴,除 烦解燥。但气味轻清,功亦甚缓,必宜久服始效,不可贵以近功。惟目痛骤用之,成功甚速,余.财俱迂缓始能取效也。近人多种菊而不知滋补方,问有用之者,又 止取作茶茗之需以为明日也。然而。甘菊花不但明目,可以大用之者,全在退阳明之胃火。盖阳明内热,必宜阴寒之药以泻之。如石膏、知母之类。然石膏过于太 竣,未免太寒。
以损胃气。不若用甘菊花至一二两,同元参、麦冬共济之,既能平胃中之火,而不伤胃中之气也。
或问:甘菊花治目最效,似乎肝经之专药,而吾子独云可退阳明之胃火,不识退阳明何等之火病耶?夫甘菊花,凡有胃火,俱可清之,而尤相宜者,痿病也。瘘病, 责在阳明。然而治阳明者,多用白虎汤,而石膏过于寒凉.恐伤胃气。而瘘病又多是阳明之虚热,白虎汤又泻实火之汤也,尤为不宜。不若用甘菊花一、二两,煎汤 以代茶饮。既退阳明之火,而又补阳明之气,久服而痿病自痊。甘菊花退阳明之火病,其在斯乎。
或问:甘菊花,人服之延龄益算。至百岁外仙去者,有之乎?抑好事者之言也?吾子既遇异人传异术,必有所闻,幸勿自秘。曰:予实未闻也。或人固请,乃喟然叹 曰:吾今而后,不敢以异术为一人延龄益算之资也,敢不罄传,与天下共之乎。夫菊得天地至清之气,又后群卉而自芳,傲霜而香,挹露而葩,而花又最耐久,是草 木之种,而欲与松柏同为后凋也,岂非长生之物乎。但世人不知服食之法,徒作茶饮之南非,又不识何以修合,是弃神丹于草莽,可惜也。我今将异人所传,备书于 后,原人依方服食,入仙不难。岂独延龄益算已哉。方名菊荚仙丹。采家园黄菊花三斤,晒干,人人参三两、白术六两、黄芪十两、干桑椹十两、熟地一斤、生地三 两、茯苓六两。当归一斤、远志四两、巴戟天一斤、枸杞子一斤、花椒三两、山药四两、茯神四两、菟丝八两、杜仲八两,各为细末,蜜为丸,白滚水每日服五钱。
三月之后,自然颜色光润,精神健强,返老不童。可以久服,既无火盛之虞,又有添精之益,实可为娱老之方也,勿以铎之轻传。而易视火元能。盖菊英为仙人所采,实有服之而仙去者,非好事者之谈,乃成仙之实录也。
或疑甘菊花药味平常,未必服之可以延龄。古人采食而仙去者,徒虚语耳。嗟乎。
采菊英而仙去,吾不敢谓古必有是人。然菊英仙丹,实异人授铎。吾睹其方中之配合得宜,既无燥热之忌,实多滋益之良,服之即不能成仙,未必不可藉以难老也。
或疑甘菊花治目,杭人多半作茶饮,而且疾未见少者,是菊花非明目之药,而菊英仙丹亦不可信之方矣。嗟乎。菊花明目,明虚人之目,而非明有病人之目 也。有病之目,即可用菊花治。亦必与发散之药同治,而不可单恃之以去风去火也。夫人之疾病不常。而人之慎疾各异。菊花之有益于人目者甚多。岂可因一二病目 成于外感,而即疑菊花之非明目也,亦太拘矣。若菊英仙丹,纯是生气生精之神药,非止明目已也。又乌可因杭城之病目,疑菊而并疑仙丹哉。
或疑真菊益龄,野菊泄人,有之乎?曰:有之。或日有之,而子何以不载也?夫菊有野种、家种之分,其实皆感金水之精英而生者也。但家种味甘,补多于泻;野菊 味苦,泻多于补。欲益精以平肝,可用家菊。欲息风以制火,当用野菊。人因《本草》之书有泄人之语,竟弃野菊不用,亦未知野菊之妙。除阳明之焰,正不可用家 菊也。
薏苡仁薏苡仁,味甘,气微寒,无毒。人脾、肾二经,兼入肺。疗湿痹有神,舒筋骨拘挛,止骨中疼痛,消肿胀,利小便,开胃气,亦治肺痈。
但必须用至一、二两,始易有功,少亦须用五钱之外,否则,力薄味单耳。薏仁最善利水,又不损耗真阴之气。凡湿感在下身者,最宜用之。视病之轻重,准甩药之多寡,则阴阳不伤,而湿病易去。人见用药之多,动生物议。
原未知药性,无怪其然。余今特为阐明,原世人勿再疑也。凡利水之药,俱宜多用,但多用利水之药,必损真阴之气,水未利,而阴且虚矣,所以他利水之药,不敢 多用。惟薏仁利水,而又不损真阴之气,诸利水药所不及者也。可以多用,而反不用,与不可多用,而反大用者,安得有利乎。故凡遇水湿之症,用慧仁一、二两为 君,而佐之健脾去湿之味,未有不速于奏效者也。倘薄其气味之平和而轻用之,无益也。
或问:薏仁味薄而气轻,何以利水之功犹胜?盖薏仁感土气而生,故利气又不损阴。
所以可多用以出奇,而不必节用以畏缩也。
或问:薏仁有取之酿酒者,亦可藉为利湿之需乎?夫薏仁性善利湿,似乎所酿之酒,亦可以利湿也。然用薏酒以治湿,而湿不能去,而特湿不能去,而湿且更重,其 故何哉?酒性大热,薏仁既化为酒,则薏仁之气味亦化为热矣,既化为热,独不可化为湿乎。湿热以治湿热,又何宜哉。此薏仁之酒,断不可取之,以治湿热之病 也。
或问:薏仁可以消瘴气,而未言及,岂忘之耶?非忘也。薏仁止能消湿气之瘴,而不能消岚气之瘴。虽岚气即湿气之然,然而湿气从下受,而岚气从上感,又各不同。薏仁消下部之湿,安能消上部之湿哉。
或问:薏仁得地之燥气,兼禀乎天之秋气,似与治痿相宜,何子忘之也?亦未曾忘也。经曰:治痿独取阳明。阳明者,胃与大肠也。二经湿热则成痿,湿去则热亦随 解。故治痿者,必去湿也。吾前言用薏仁至一、二两者,正言治痿病也。天下惟痿病最难治,非多用薏仁,则水不易消,水不消,则热不能解,故治痿病断须多用 耳。推之而凡有诸湿之症,无不宜多用。正不可因铎之未言,即疑而不用也。
或问:薏仁功用甚薄,何不用猪苓、泽泻,可以少用见功,而必多用薏仁,何为乎?不知利水之药,必多耗气,薏仁妙在利水而又不耗真气,故可重用之耳。
山药山药,味甘,气温平,无毒。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人脾、胃。治诸虚百损,益气力,开心窍,益知慧,尤善止梦遗,健脾开胃,止泻生精。山药可君可臣,用 之无不宜者也,多用受益,少用亦受益,古今颇无异议,而余独有微辞者,以其过于健脾也。夫人苦脾之不健,健脾,则大肠必坚牢,胃气必强旺而善饭,何故独取 而贬之?不知脾胃之气太弱,必须用山药以健之,脾胃之气太旺,而亦用山药,则过于强旺,反能动火。世人往往有胸腹饱闷,服山药而更甚者,正助脾胃之旺也。 人不知是山药之过,而归咎于他药,此皆不明药性之理也。盖山药人心,引脾胃之邪,亦易人心。山药补虚,而亦能补实,所以能添饱闷也。因世人皆信山药有功而 无过,特为指出,非贬山药也。山药舍此之外,别无可议矣。
或问:山药用乃补阴精之物,而吾子谓是健脾胃之品,何子之好异也?曰:山药益人无穷,损人绝少。余谈《本草》,欲使其功过各不掩也。山药有功而无过。言其 能助脾胃之火者,是求过于功之中也。然而天下之人脾胃太旺者,千人中一、二,不可执动火之说,概疑于脾胃之未旺者,而亦慎用之也。脾胃未旺,则肾气必衰, 健脾胃正所以补阴精也。予道其常,何好异之有。
或问:山药补肾,仲景张公所以用之于六味地黄丸中也,然而山药实能健脾开胃,意者六味丸非独补肾之药乎?曰:六味丸实直补肾水之药也,山药亦补肾水之药, 同群共济何疑。然而,六味丸中之用山药,意义全不在此。山药,乃心、肝、脾、肺、肾无经不入之药也。六味丸虽直补肾中之水,而肾水必分资于五脏,而五脏无 相引之使,又何由分布其水,而使之无不润乎。
倘别用五脏佐使之品。方必杂而不纯,故不若用山药以补肾中之水。而又可遍通于五脏。此仲景张夫子补一顾五,实有鬼神难测之机也。
或问:山药入于六味丸中之义,予既巳闻之,不识入于八味丸中,亦有说乎?曰:八昧丸,由六味而加增者也,似乎知六味,即可知八味之义矣。谁知八味丸中之用 山药,又剔有妙义乎。六昧,补肾中之水;而八味,则补肾中之火也。补肾中之火者,补命门之相火也。夫身之相火有二:一在肾之中,一在心之外。补肾中之相 火,则心外之相火,必来相争,相争则必相乱,宜豫有以安之,热必下朴肾中之火,即当上补心下之火矣。然而既因肾寒而补其下,又顾心热以补其上,毋论下不能 温其寒,而上且变为热矣。用药之杂,可胜叹哉。妙在用山药于八味丸中,山药人肾者十之七,人心者十之三,引桂、附之热,多温于肾中,少温于心外,使心肾二 火各有相得,而不致相争,使肾之气通于心,而心之气通于肾,使脾胃之气安然健运于不息,皆山药接引之功也。仲景公岂漫然用之哉。
或疑山药不宜多用,何以六味地黄丸终年久服而无害也,得毋入于地黄丸可以多用,而入于他药之中即宜少用耶?不知山药可以多用而无忌。吾前言脾健之人宜忌者,虑助火以动燥,而非言其不可以多用也。
或疑山药津滑,何能动燥?曰:山药生精,自然非助燥之物。吾言其助燥者,助有火之人,非助无火之人也。
或问:山药色白,何能乌须,何吾子用之为乌须圣药?日;山药何能乌须哉。山药入肾,而尤通任督。任督之脉,上行于唇颊,故山药用之于乌芝麻、黑豆、地黄、 南烛、何首乌之内,导引以黑须鬓,非山药之能自乌也。或又问山药既为引导之药,则不宜重用之为君矣。不知山药虽不变白,而性功实大补肾水者也。肾水不足 者,须鬓断不能黑,我所以重用山药而奏功也。
知母知母,味苦、辛,气大寒,沉而降,阴也,无毒。入足少阴、阳明,又人手太阴。最善泻胃、肾二经之火,解渴止热,亦治久疟。此物止可暂用,而不可久服。 丹溪加入六味丸中,亦教人暂服,以泻肾中浮游之火,非教人长服也。近世竟加知母、黄柏,谓是退阴虚火热之圣方,令人经年长用,以致脾胃虚寒,不能饮食,成 痨成瘵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幸薛立斋、赵养葵论知母过寒,切戒久食,实见到之语,有功于世。总之,此物暂用,以泻胃中之火,实可夺命;久用,以补肾中之 水,亦能促命。
谓知母竟可杀人,固非立论之纯,谓知母全可活人。亦非持说之正也。
或问:知母泻肾,肾有补而无泻,不可用知母,宜也。若用之以泻胃,似可常用,何吾子亦谓止可暂用乎?曰:胃火又何可常泻也,五脏六腑皆仰藉于胃,胃气存则 生,胃气亡则死。胃中火盛,恐其消烁津液,用石膏、知母以救胃,非泻胃也。然而石膏过于峻削,知母过于寒凉,胃火虽救,而胃土必伤。故亦宜暂用以解氛,断 不宜常用以损气也。
或问:知母古人皆言是补肾滋阴妙药,吾子乃言是泻火之味,此余所以疑也。不知母疑也。天下味温者能益人,未闻苦寒者而亦益也。知母苦而大寒,其无益于脾 胃,又何必辨。惟是既无益于脾胃,何以泻胃中之火,能夺命于须臾乎。似乎泻即补之之义了。然而暂用何以相宜,久用何以甚恶?是泻火止可言救肾,而终不可言 补肾也。
或问:知母性过寒凉,久服损胃,何不改用他药以救胃,而白虎汤中必用知母,以佐石膏之横,不以寒济寒乎?嗟乎。何问之善也。
夫白虎汤,乃治胃火之初起,单用石膏以救胃,犹恐不胜,故又加知母,以止其肾中之火,使胃火之不增焰也。若胃火已炽之后与将衰之时,知母原不必加入之也。或去知母,而易之天冬、元参之味,亦未为不可也。
或问:知母、黄柏用之于六味丸中,朱丹溪之意以治阴虚火动也,是岂无见者乎?嗟乎。阴虚火动,六味汤治之足矣,何必又用知母、黄柏以泻火乎。夫火之有余, 因水之不足也,补其水,则火自息矣。丹溪徒知阴虚火动之义,而加入二味,使后人胶执而专用之,或致丧亡,非所以救天下也。
或问:知母既不宜轻用,何不竟删去之,乃既称其功,又辟其过耶?嗟乎。吾言因丹溪而发,岂谓知母之等于鸠毒哉。盖知母止可用之以泻胃火之有余,而不可用之以泻肾火之不足,故泻胃火则救人,而泻肾火则杀人也。丹溪止主泻肾,而不主泻胃,此生死之大关,不可不辨也。
或问:李时珍发明知母是气分之药,黄柏是血分之药。黄柏入肾,而不人肺;知母下润肾,而上清肺金,二药必相须而行。譬之是之不能离水母也。是黄柏、知母, 必须同用为佳,而吾子谓二药不可共用,得毋时珍非欤?曰:时珍殆读书而执者也。不知黄柏未尝不入气分,而知母未尝不入血分也。黄柏清肾中之火,亦能清肺中 之火;知母泻肾中之热,而亦泻胃中之热。胃为多气多血之腑,岂止入于气分,而不入于血分耶?是二药不必兼用,不可即此而悟哉。
金钗石斛金钗石斛,味甘、微苦,性微寒,无毒。不可用竹斛、木斛,用之无功。石斛却惊定志,益精强阴,尤能健脚膝之力,善起痹病,降阴虚之火,大有殊功。 今世吴下之医,颇喜用之,而天下人尚不悉知其功用也。盖金钗石斛,生于粤闽岩洞之中,岩洞乃至阴之地,而粤闽又至阳之方也,秉阴阳之气以生,故寒不为寒, 而又能降虚浮之热。夫虚火,相火也,相火宜补,而不宜泻。金钗石斛妙是寒药,而又有补性,且其性又下行,而不上行。若相火则易升,而不易降者也,得石斛则 降而不升矣。夏月之间,两足无力者,服石斛则有力,岂非下降而兼补至阴之明验乎。故用黄柏、知母泻相火者,何如用金钗石斛之为当乎。
盖黄柏、知母泻中无补,而金钗石斛补中有泻也。
或问:金钗石斛降阴虚之火,乃泻阴之物也,何以能健脚膝之力,其中妙义,尚未畅发。
曰:肾有补而无泻,何以金钗石斛泻肾,而反补肾,宜子之疑也。余上文虽已略言之,而今犹当罄言之。夫肾中有水、火之分,水之不足,火之有余也;火之有余, 水之不足也。是水火不能两平者,久矣。脚膝之无力者,肾水之不足也。水不足则火觉有余,火有余则水又不足,不能制火矣。不能制火,则火旺而熬干骨中之髓, 欲其脚膝之有力也,必不得之数矣。金钗石斛,本非益精强阴之药,乃降肾中命门虚火之药也,去火之有余,自然益水之不足,泻肾中之虚火,自然添骨中之真水 矣,故曰:强阴而益精。此脚膝之所以健也。然则黄柏、知母亦泻肾火之药,何以不能健脚膝?不知肾中之火,大寒则泻而不补,微寒则补而能泻。此金钗石斛妙在 微寒,以泻为补也。
或问:子恶用黄柏,知母之泻火,何又称金钗石斛?不知金钗石斛,非知母、黄柏可比。知母、黄柏大寒,直入于至阴,使寒入于骨髓之中。金钗石斛不过微寒,虽入于至阴,使寒出于骨髓之外,各有分别也。
或疑金钗石斛使寒出于骨髓,实发前人之未发,但无徼难信耳。曰:石斛微寒,自不伤骨,骨既不伤,则骨中之热自解,骨中热解,必散于外,此理之所必然,不必有徵而后信也。
肉苁蓉肉苁蓉,味甘温而咸、酸、无毒。人肾。
最善兴阳,止崩漏。久用令男女有子,暖腰膝。但专补肾中之水火,余无他用。若多用之,能滑大肠。古人所以治虚人大便结者,用苁蓉一两,水洗出盐味,另用净 水煮服,即下大便,正取其补虚而滑肠也。然虽补肾,而不可专用,佐人参、白术、熟地、山茱萸诸补阴阳之药,实有利益。使人阳道修伟,与驴鞭同用更奇,但不 可用琐阳。盖琐阳非苁蓉可比,苁蓉,乃马精所化,故功效能神;琐阳,非马精所化之物,虽能补阴兴阳,而功效甚薄,故神农薄而不取。近人舍苁蓉,而用琐阳, 余所以分辨之也。至于草苁蓉,尤不可用。凡用肉苁蓉,必须拣其肥大而有鳞甲者,始可用。否则,皆草苁蓉而假充之者,买时必宜详察。
或问:肉苁蓉既大补,又性湿无毒。多用之正足补肾,何以反动大便?不知肉苁蓉肉,乃马精所化之物,马性最淫,故能兴阳。马精原系肾中所出,故又益阴。然而马性又最动。
故骤用之多,易动大便,非其味滑也。
或问:肉蓉之动大便,恐是攻剂,而非补药也?夫苁蓉,乃有形之精所生,实补而非泻。试观老人不能大便者,用之以通大便。
夫老人之闭结,乃精血之不足,非邪火之有余也,不可以悟其是补而非攻乎。
或疑肉苁蓉性滑而动大便,凡大肠滑者,可用乎,抑不可用乎?夫大肠滑者,多由于肾中之无火,肉苁蓉兴阳,是补火之物也。补火而独不能坚大肠乎。故用之而滑者,久用之而自涩矣。
或疑肉苁蓉,未必是马精所生,此物出之边塞沙土中,岁岁如草之生,安得如许之马精耶?曰:肉苁蓉,是马精所生,非马精所生,吾何由定。但此说,实出于神农之《本草》,非后人之私臆也。肉苁蓉不得马精之气,而生于苦寒边塞之外,又何能兴阳而补水火哉。
或问:王好古曾云:"服苁蓉以治肾,必妨于心",何子未识也?曰:此好古不知苁蓉,而妄诫之也。凡补肾之药,必上通于心.心得肾之精,而后元焦枯之患。苁蓉大补肾之精,即补心之气也。又何妨之有。
补骨脂补骨脂,即破故纸也。味苦、辛,气温,无毒。入脾、肾二经。治男子劳伤,疗妇人血气,止腰膝酸疼,补髓添精,除囊涩而缩小便,固精滑而兴阳事,手足 冷疼,能定诸逆气。但必下焦寒虚者,始可久服。倘虚火太旺,止可暂用,以引火归原,否则,日日服之,反助其浮游之火上升矣。古人用破故纸,必用胡桃者,正 因其性过于燥,恐动相火,所以制之使润,非故纸必须胡桃也。
或问:补骨脂既不可轻用,而青娥等丸,何以救人终日吞服,又多取效之神耶?不知青娥丸,治下寒无火之人也。下寒无火者,正宜久服,如何可禁其少用乎。命门火衰,以致腰膝之酸疼,手足之逆冷,甚则阳痿而泄泻。
苟不用补骨脂,急生其命门之火,又何以回阳而续命乎。且补骨脂尤能定喘,肾中虚寒,而关元真气上冲于咽喉,用降气之药不效者,投之补骨脂,则气自归原,正藉其温补命门,以回审而定喘也。是补骨脂,全在审其命门之寒与不寒而用之耳,余非不教人之久服也。
或问:破故纸虽善降气,然亦能破气,何子未言也?曰:破故纸,未尝破气,人误见耳。
破故纸,乃纳气归原之圣药,气之不归者。尚使之归,岂气之未破者而使之破乎?惟是性过温,恐动命门之火,火动而气动,气动而破气者有之。然而用故纸者,必 非单用,得一、二味补阴之药以济之,则火且不动,又何能破气哉?或问:补骨脂治泻有神,何以脾泻有宜有不宜乎?不知补骨脂,非治泻之药,不治泻而治泻者, 非治脾泄,治肾泄也。肾中命门之火寒,则脾气不固,至五更痛泻者,必须用补骨脂,以温补其命门之火,而泻者不泻矣。若命门不寒而脾自泻者,是有火之泻,用 补骨脂正其所恶,又安能相宜哉。
或问:补骨脂无胡桃,犹水母之无虾,然否?嗟乎。破故纸何藉于胡桃哉。破故纸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包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不必胡桃之油润之,始能人心入肾也。盖破故纸,自有水火相生之妙,得胡桃仁而更佳,但不可谓破故纸,必有藉于胡桃仁也。
或疑破故纸阳药也,何以偏能补肾?夫肾中有阳气,而后阴阳有既济之美。破故纸,实阴阳两补之药也,但两补之中,补火之功多于补水。制之以胡桃仁,则水火两得其平矣。
或问:破故纸补命门之火,然其气过燥,补火之有余,恐耗水之不足。古人用胡桃以制之者,未必非补水也。不知胡桃以制破故纸者,非制其耗水也,乃所以助肾中之火也。
盖肾火非水不生,胡桃之油最善生水,肾中之水不涸,则肾中之火不寒,是破故纸得胡桃,水火有两济之欢也。
羌活附独活羌活,味苦、辛,气平而温,升也,阳也,无毒。入足太阳、足少阴二经,又入足厥阴。善散风邪,利周身骨节之痛,除新旧风湿,亦止头痛齿疼。古人谓羌活系君药,以其拨乱反正,有旋转之力也,而余独以为止可充使,而并不可为臣佐。
盖其味辛而气升,而气过于散,可用之为引经,通达上下,则风去而湿消。若恃之为君臣,欲其调和气血,燮理阴阳,必至变出非常,祸生反掌矣。故羌活止可加之于当、芎、术、苓之内,以逐邪返正,则有神功耳。羌活与独活,本是两种,而各部《本草》俱为一种者,误。
仲景夫子用独活,以治少阴之邪,东垣先生用羌活,以治太阳之邪,各有取义,非取紧实者谓独活,轻虚者谓羌活也。盖二物虽同是散邪,而升降之性各别,羌活性升,而独活性降。
至于不可为君臣,而止可充使者,则彼此同之也。
或问:九味羌活汤,古人专用之以散风寒之邪,今人无不宗之,而吾子贬羌活为充使之药,毋乃太轻乎?曰:羌活虽散风邪,而实能损正,邪随散解,正亦随散而俱 解矣。九味羌活汤,杂而不纯,余最不取。外感风邪治法,安能出仲景夫子之范围;内伤而兼外感治法,安能出东垣先生之范围。余治外感,遵仲景夫子;治内伤之 外感,遵东垣先生,又何风邪之不去,而必尚九味羌活汤为哉。
或疑洁古老人创造九味羌活汤,以佐仲景公之不逮,是其半生学问,全在此方。而先生薄羌活,而并轻其方,窃谓先生过矣?嗟乎!洁古创造九味羌活汤者,因仲景 公方法不明于天下,而东垣先生尚未创制补中益气之汤。不得已而立此方,以治外感,实所以治内伤也。今东垣先生既立有补中益气汤,实胜于九味羌活汤远甚,又 何必再用洁古之方哉。至于治外感之法,莫过仲景公伤寒书之备。外感善变,岂羌活区区一方,即可以统治六经传经之外感耶。况仲景公伤寒书,经铎与喻嘉言之阐 发而益明,故外感直用其方,断乎无疑。若九味羌活汤,实可不用。洁古老人半生精力。徒耗于此方,杂而不纯,亦何足尚,余是以轻之,岂为过哉。
或谓:羌活、独活同时散药,羌活性升,而独活性降,升则未免有浮动之虞,与其用羌活。不若用独活之为安。嗟乎。有邪宜散,升可也,降亦可也。无邪可散,散药均不可用,又何论于升降乎。况二味原自两种,散同而升降各别,又乌可乱用之哉。
柴胡柴胡,味苦,气平,微寒。气味俱轻,升而不降,阳中阴也。无毒。人手足少阳、厥阴之四经。泻肝胆之邪,去心下痞闷,解痰结,除烦热,尤治疮疡,散诸经 血凝气聚,止偏头风,胸协刺痛,通达表里邪气,善解潮热。伤寒门中必须之药,不独疟症、郁症之要剂也。妇人胎产前后,亦宜用之。目病用之亦良,但可为佐 使,而不可为君臣。盖柴胡入于表里之间,自能通达经络,故可为佐使,而性又轻清微寒,所到之处,春风和气,善于解纷,所以用之,无不宜也。然世人正因其用 无不宜,无论可用不可用,动即用之。如阴虚痨瘵之类,亦终日煎服,耗散真元,内热更炽,全然不悟,不重可悲乎。夫柴胡止可解郁热之气,而不可释骨髓之炎 也,能入于里以散邪,不能入于里以补正,能提气以升于阳。使参、芪、归、术,共健脾而开胃,不能生津以降于阴,使麦冬、丹皮,同益肺以滋肾,能入于血室之 中以去热,不能入于命门之内以去寒。无奈世人妄用柴胡以杀人也,余所以探辨之耳。
或问:柴胡不可用之以治阴虚之人是矣,然古人往往杂之青蒿、地骨皮、丹皮、麦冬之内,每服退热者,又谓之何?曰:此阴虚而未甚者也。夫阴虚而火初起者,何妨少用柴胡,引诸补阴之药,直入于肝、肾之间,转能泻火之速。所恶者,重加柴胡,而又久用不止耳。
用药贵通权达变,岂可拘泥之哉。
又问:柴胡既能提气,能补脾而开胃,何以亦有用之而气上冲者,何故?此正见柴胡之不可妄用也。夫用柴胡提气而反甚者,必气病之有余者也。气之有余,必血之 不足也,而血之不足也,必阴之甚亏也。水不足以制火,而反助气以升阳,则阴愈消亡,而火愈上达,气安得而不上冲乎。故用柴胡以提气,必气虚而下陷者始可。至于阴虚火动之人,火正炎上,又加柴胡以升提之,火愈上腾,而水益下走,不死何待乎?此阴虚火动,断不可用柴胡,不更可信哉。
或问:柴胡乃半表半里之药,故用之以治肝经之邪最效,然而肝经乃阴脏也,邪入于肝,已入于里矣,又何半表半里之是云。
乃往往用柴胡而奏效如神者,何也?夫肝经与胆经为表里,邪入于肝,未有不入于胆者,或邪从胆而入于肝,或邪已人肝,而尚留于胆,彼此正相望而相通也。柴胡乃散肝邪,而亦散胆邪之药,故入于肝者半,而入于胆者亦半也。所以治肝而胆之邪出,治胆而肝之邪亦出也。
或问:柴胡既是半表半里之药,邪入于里,用柴胡可引之以出于表,则病必轻。邪人于表,亦用柴胡,倘引之以入于里,不病增乎?不知柴胡乃调和之药,非引经之 味也。邪入于内者,能和之而外出,岂邪入于内者,反和之而内人乎。此伤寒汗、吐、下之病,仲景夫子所以每用柴胡,以和解于半表半里之间,使反危而为安,拨 乱而为治也。
又闯:柴胡既是调和之药,用之于郁症者固宜,然有时解郁,而反动火,又是何故?此必妇女郁于怀抱,而又欲得男子,而不可得者也。论妇女思男子而不可得之 脉,肝脉必大而弦出于寸口。然其怀抱既郁,未用柴胡之前,肝脉必涩而有力,一服柴胡,而涩脉必变为大而且弦矣。郁开而火炽,非柴胡之过,正柴胡之功,仍用 柴胡,而多加白芍、山栀,则火且随之而即散矣。
或问:柴胡为伤寒要药,何子不分别言之?曰:伤寒门中,柴胡之症甚多,何条宜先言,何条宜略言乎。虽然柴胡之症虽多,而其要在寒热之往来,邪居于半表半里之言尽之矣,用柴胡而顾半表半里也,又何误用哉。
或问:柴胡开郁,凡男子有郁,亦可用之乎?盖一言郁,则男妇尽在其中矣,岂治男一法,而治女又一法乎。世人治郁,多用香附,谁知柴胡开郁。更易于香附也。
或问:柴胡本散风之味,何散药偏能益人,此予之未解也。盖克中不克,克即是生也。柴胡入肝,而性专克木。何以克木而反能生木?盖肝属木,最喜者水也,其次则喜风。然风之寒者,又其所畏,木遇寒风则黄落,叶既凋零,而木之根必然下生而克土矣。
土一受伤,而胃气即不能开而人病,似乎肝之不喜风也,谁知肝不喜寒风,而喜温风也。木一遇温风,则萌芽即生,枝叶扶疏,而下不生根,又何至克土乎。土不受 伤,而胃气辄开,人病顿愈。柴胡,风药中之温风也,肝得之而解郁,竟不知抑滞之气何以消释也。故忘其性之相制,转若其气之相宜。克既不克,非克即所以生之 乎。克即是生,克非真克,生乃是克,生实非生。全生于克之中,制克于生之外,是以反得其生之之益,而去其克之之损也。
或疑柴胡用之于补中益气汤,实能提气,何以舍补中益气汤用之,即不见有功,意者气得补而自升,无藉于柴胡耶?曰:柴胡提气,必须于补气之药提之,始易见功,舍补气之药,实难奏效。盖升提之力,得补更大,非柴胡之不提气也。
或疑柴胡用之补中益气汤中,为千古补气方之冠,然吾以为柴胡不过用之升提气之下陷耳,胡足奇。此真不知补中益气汤之妙也。补中益气汤之妙,全在用柴胡,不可与升麻并论也。盖气虚下陷,未有不气郁者也。
惟郁故其气不扬,气不扬,而气乃下陷,徒用参、归、芪、术以补气,而气郁何以舒发乎。即有升麻以提之,而脾胃之所,又因肝气之郁来克,何能升哉。得柴胡同 用舒肝,而肝不克土,则土气易于升腾。方中又有甘草、陈皮,以调和于胸膈之间,则补更有力,所以奏功如神也。是柴胡实有奇功,而非提气之下陷一语可了。使 柴胡止提气之下陷,何风药不可提气,而东垣先生必用柴胡,以佐升麻之不及耶。夫东垣先生一生学问,全在此方,为后世首推,盖不知几经踌度精思,而后得之 也,岂漫然哉。
或问:大、小柴胡汤,俱用柴胡,何以有大小之分,岜以轻重分大小乎?不知柴胡调和于半表半里,原不必分大小也,而仲景张夫子分之者,以大柴胡汤中有攻下之药,故以大别之。实慎方之意,教人宜善用柴胡也,于柴胡何豫哉。
升麻升麻,味苦、甘,气平、微寒,浮而升,阳也,无毒。入足阳明、太阴之经。能升脾胃之气。得白芷、葱白同用,又入手阳明太阴二经,其余他经,皆不能人。 能辟疫气,散肌肤之邪热,止头、齿、咽喉诸痛。并治中恶,化斑点疮疹,实建奇功。疗肺痈有效,但必须同气血药共用。可佐使,而亦不可以为君臣。世人虑其散 气,不敢多用也,然而,亦有宜多用之时。本草如《纲目》、《经疏》,尚未及言,况他书乎。夫升麻之可多用者,发斑之症也。
凡热不太甚,必不发斑,惟其内热之甚,故发出于外,而皮毛坚固,不能遽出,故见斑而不能骤散也。升麻原非退斑之药,欲退斑,必须解其内热,解热之药,要不 能外元参、麦冬与芩、连、栀子之类。然元参、麦冬与芩、连,栀子,能下行,而不能外走,必藉升麻,以引诸药出于皮毛,而斑乃尽消。倘升麻少用,不能引之出 外,势必热走于内,而尽趋于大、小肠矣。
夫火性炎上,引其上升者易于散,任其下行者难于解。此所以必须多用,而火热之毒,随元参、麦冬与芩、连、栀子之类而行,尽消化也。
大约元参、麦冬用至一、二两者,升麻可多用至五钱,少则四钱、三钱,断不可止用数分与一钱已也。
或问:升麻能止衄血,先生置而不讲,岂仲景张夫子非欤?曰:以升麻为止血之药,此不知仲景夫子用升麻之故也。夫吐血出于胃。衄血出于肺。止血必须地黄,非 升麻可止。用升麻者,不过用其引地黄,入于肺与胃耳。此等病,升麻又忌多用,少用数分,便能相济以成功,切不可多至于一钱之外也。
又问:升麻升而不降,何以大便闭结反用升提,必取于升麻,岂柴胡不可代耶?曰:升麻与柴胡,同是升提之药,然一提气而一提血。大便燥急,大肠经之火也。大 肠有火,又由于肾水之涸也。欲润大肠,舍补血之药无由,而补血又贵之补肾,使肾之气通于大肠,而结闭之症可解。然则通肾之气,以生血可也,而必加升麻于补 肾、补血之中者,盖阴之性凝滞而不善流动,取升麻而升提其阴气,则肺金清肃之令行。况大肠与肺又为表里,肺气通,而大肠之气亦通,肺气通,而肾之气更通, 所以闭者不闭,而结者不结也。若用柴胡,虽亦入肝,能提升血分之气,终不能入于大肠,通于肺、肾之气,此柴胡之所以不可代升麻也。
或问:升麻与犀角迥殊,何以古人有无犀角,用升麻代之之语,以升麻、犀角同属阳明也,然否?夫升麻虽与犀角同属阳明,而仲景夫子用升麻以代犀角,非特为其同属阳明也。
犀角地黄汤所以治肺经之火也,犀角引地黄以至于肺,而升麻亦能引地黄以至于肺也。
肺与大肠为表里,清肺而大肠阳明之火自降,瘀血必从大便而出,是升麻清肺,正所以清阳明也。
或同:升麻用之于补中益气汤中,岂虑柴胡不能升举,故用之以相佐耶?曰:柴胡、升麻同用之补中益气汤者,各升提其气,两不相顾,而两相益也。柴胡从左而升 气,升麻从右而提气,古人已言之矣。然而柴胡左升气,而右未尝不同提其气,升麻右提气,而左亦未尝不共升其气,又两相顾,而两相益也。
车前子车前子,味甘、咸,气微寒,无毒。入膀胱、脾、肾三经。功专利水,通尿管最神,止淋沥泄泻,能闭精窍,祛风热,善消赤目,催生有功。但性滑,利水可 以多用,以其不走气也;泻宜于少用,以其过于滑利也。近人称其力能种子,则误极矣。夫五子衍宗丸用车前子者,因构杞、覆盆过于动阳,菟丝、五味子过于涩 精,故用车前以小利之。用通于闭之中,用泻于补之内,始能利水而不耗气。水窍开,而精窍闭,自然精神健旺,入房始可生子,非车前之自能种子也。大约用之补 药之中,则同群共济,多有奇功。未可信是种子之药,过于多用也。
或问:车前利水之物,古人偏用之,以治梦遗而多效者,何也?曰:此即余上文所言,尿窍开而精窍闭也,然而车前之能闭精,又不止此。车前最泻膀胱之火,火邪 作祟,煽动精门,则生淫邪之梦。用车前以利膀胱,则火随水散,精门无炎蒸之煽动,则肾中之精气自安,神不外走,自无淫邪之梦,又何至阴精之外泄乎。此种秘 理,前人未谈,予实得之扁鹋公之传也。
或问:《诗经》载苤芑为催生之药。苤芑,即车前子草也,果可备之为催生乎?曰:车前子性滑,自易于生产,然而不可单藉车前子也。凡产妇之易于生产者,必以 气血旺健之主,气足则儿之身易于转头,血旺则儿之身易于出户。使气怯则儿无力,难于速转,血涸则胞无浆,难于顺送。使不补其气血,而惟图车前之滑胞,吾恐 过利其水,胎胞干燥,转难生产。必须于补气、补血之中,而佐车前子之滑利,庶几催生有验乎。
或问:缪仲醇注车前子,说男女阴中有二窍,一通精,一通水。命门真阳之火,道家谓之君火。膀胱湿热,浊阴之水,渗出窍外为小便,道家谓之民火,民火二字甚新,何以《内经》、《灵枢》未言也?嗟乎。此臆说也。夫人身之火止二,一君火,一相火也,安有民火哉。
此好异而过者也。其言二窍不并开,水窍开,而精窍闭,车前利水而能闭精,实阐微之论。
或问:车前子孕妇宜戒,嫌其过滑以堕胎也。曰:车前子利水而不耗气,气既不耗,又何能堕胎。惟是过于利水,日用车前,未免气不耗,而胎浆太干,恐有难于生 产之虞。然古之妇人采苤芑以滑胎者,乃取之备临产之用,非恃之易产,而日日常饮也。然则孕妇因小水不利,偶一用之,何损于胎乎。竟戒绝口不服,岂知车前 哉。
蒺藜子蒺藜子,味甘、辛,气温、微寒,无毒。沙苑者为上,白蒺藜次之,种类各异,而明目去风则一。但白蒺藜善破症结,而沙苑蒺藜则不能也。沙苑蒺藜善止遗 精遗溺,治白带喉痹,消阴汗,而白蒺藜则不能也。今世专尚沙苑之种,弃白蒺藜不用,亦未知二种之各有功效也,余所以分别而并论之。
或问:蒺藜能催生堕胎,而先生略之,岂著《本草》者误耶?夫蒺藜无毒之药,何能落胎,谓其催生,而性又不速。然则从前《本草》,何所据而言之耶。见白蒺藜之多刺耳。
凡刺多者,必有碍于进取,留而不进则有之,朱闻荆棘之中,反行之而甚速者也。是蒺藜既不能催生,又何能堕胎哉。且沙苑蒺藜,乃解火之味,凡妇人堕胎,半由于胎气之太热。
古人谓黄芩能安胎者,正取其寒而能去火也。
况蒺藜微寒,不同于黄芩之大冷,而性又兼补,且能止精之滑,安有止精涩味,而反堕胎者乎。此传闻者之误,不足信也。
或问:蒺藜,以同州沙苑者为胜,近人以之治目,谓补而又明目也。先生又云与白蒺藜同为明目之药。岂同州者非补,而白蒺藜反补耶?曰:二味各有功效,余上文 已言之矣。而吾子又问,余更当畅谈之。沙苑蒺藜,补多而泻少;白蒺藜,泻多而补亦多。沙苑蒺藜补肝肾而明目,乃补虚火之目,而不可补实邪之目也,朴实邪之 目,则日转不明,而羞明生瘴之病来矣;白蒺藜补肝肾而明目,乃泻实邪之目,而又可补虚火之目也,补虚火之目,则目更光明,泻实邪之目则目更清爽。二者相 较,用沙苑蒺藜以明目,反不若用白蒺藜之明目为佳,而无如近人之未知也。
青黛青黛,即靛之干者。《本草》辨其出波斯国者,始真转误矣。味苦,气寒,无毒。杀虫除热,能消赤肿疔毒,兼疔金疮,余无功效。
他书盛称之,皆不足信也,惟喉痹之症,倘系实火,可以内外兼治,而《本草》各书反不言及。大约此物,止可为佐使者也。
惟杀虫可以多用,止消一味,用至~两,研末,加入神曲三钱、使君子三钱,同为丸,一日服尽,虫尽死矣。他病不必多用,盖青黛气寒,能败胃气,久服,则饮食不能消也。
或问:青黛微物,先生亦慎用之,毋乃太过乎?嗟乎。用药一味之失,便杀一人,况发明《本草》,而可轻言之乎。故物虽至微,不敢忽也。
或问:青黛物虽至微,仲景公用以治发斑之伤寒,何子未之言及?曰:吾前育赤肿,即发斑之别名,非满身肿起为赤肿也。青黛至微,而能化斑者,以其善凉肺金之 气。肺主皮毛,皮肤之发斑,正肺之火也。然而发斑,又不止肺火,必挟胃火而同行,青黛又能清胃火,仲景公所以一物而两用之,退肺、胃之火,自易解皮肤之斑 矣。
天麻天麻,味辛、苦,气平,无毒。入肺、脾、肝、胆、心经。能止昏眩,疗风去湿,治筋骨拘挛瘫痪,通血脉,开窍,余皆不足尽信。此有损无益之药,似宜删去。然外邪甚盛,壅塞于经络血脉之问,舍天麻又何以引经,使气血攻补之味,直入于受病之中乎。故必须备载。
但悉其功用,自不致用之之误也。总之,天麻最能祛外来之邪,逐内闭之痰,而气血两虚之人,断不可轻用耳。
或问:天麻世人多珍之。何先生独戒人以轻用乎?曰:余戒人轻用者,以天麻实止可祛邪。无邪之人用之。未有不受害者也。
余所以言其功,又示其过,虑世之误用以损人也。
蒲黄蒲黄,味甘,气平,无毒。入肺经。能止衄血妄行,咯血、吐血亦可用,消瘀血,止崩漏白带,调妇人血候不齐,去儿枕痛,疗跌扑折伤,亦佐使之药,能治实。而不可治虚。虚人用之,必有泄泻之病,不可不慎也。《本草》谓其益气力,延年作仙,此断无之事,不可尽信。
或问:蒲黄非急需之药,而吾子取之以备用,不知何用也?夫蒲黄治诸血症最效,而治血症中尤效者,咯血也。咯血者,肾火上冲,而肺金又燥,治肾以止咯血,而 不兼治肺,则咯血不能止。蒲黄润肺经之燥,加入于六味地黄汤中,则一服可以奏功,非若他药如麦冬、五味,虽亦止咯,而功不能如是之捷。此所以备之,而不敢 删耳。
何首乌何首乌,味甘而涩,气微温,无毒。神农未尝非遗之也。以其功效甚缓,不能急于救人,故尔失载。然首乌蒸熟,能黑须鬓,但最恶铁器。凡人诸药之中,曾 经铁器者,沾其气味,绝无功效。世人久服而不变白者,正坐此耳,非首乌之不黑须鬓也。近人尊此物为延生之宝,余薄而不用。惟生首乌用之治疟,实有速效,治 痞亦有神功,世人不尽知也。虽然首乌蒸熟,以黑须鬓,又不若生用之尤验。盖首乌经九蒸之后,气味尽失,又经铁器,全无功效矣。不若意以石块敲碎,晒干为 末,同桑叶、茱萸、熟地、枸杞子、麦冬、女贞子、乌饭子、黑芝麻、白果,共捣为丸,全不见铁器,反能乌须鬓,而延年至不老也。
或问:何首乌蒸熟则味甘,生用则味涩,自宜制熟为黑,则白易变为黑矣,此情理之必然也,先生独云生用为佳,亦有说乎?曰:首乌制黑。犹生地之制熟也,似宜熟者之胜生。
然而首乌不同生地也,生地性寒而味苦。制熟则苦变甘,而寒变温矣,故制熟则佳。首乌味本甘而气本温,生者原本益人,又何必制之耶。况生者味涩,凡人之精,未有不滑者也,正宜味涩以止益,奈何反制其不涩,使补者不补也。余所以劝人生用之也。
或疑何首乌乃乌须圣药,不制之,何能乌须?先生谓生胜于熟,读先生之论,则实有至理,然未见先生之自效,恐世人未必信先生之言也。曰:吾谈其理,何顾吾须 之变白不变白哉。况吾须之白而乌,乌而白者屡矣,乃自不慎酒色,非药之不验也。盖服乌须之药,必须绝欲断酒,否则无功耳。
或疑何首乌既能延年,而神农未尝言,先生又薄其功用之缓,是此药亦可有可无之药也。虽然,何首乌乌可缺也,亦顾人用之何如耳。大约用之乌须延寿,其功缓,用之攻邪散疟,其功速。近人用之,多犯铁器,所以皆不能成功也。
或疑何首乌今人艳称之,吾子薄其功用,得毋矫枉之过欤?嗟乎。何首乌实有功效,久服乌须鬓,固非虚语。吾特薄其功用之缓,非薄其无功用也。如补气也,不若 黄芪、人参之捷。如补血也,不若当归、川芎之速。如补精也,不若熟地、山茱之易于见胜。此余之所以宁用彼,而不用此也。至于丸药之中,原图缓治,何首乌正 宜大用,乌可薄而弃之哉。
或问:何首乌毕竟以大者为佳,近人用何首乌而不甚效者,大抵皆细小耳,未必有大如斗者也。曰:古人载何首乌,而称极大者为神,乃夸诩之辞,非真亲服而有验 也。且何首乌小者之力胜于大者,世人未知也。近来士大夫得一大首乌,便矜奇异,如法修制,九蒸九晒,惟恐少越于古人,乃终年吞服,绝不见发之乌而鬓之黑, 可见大者功用劣于细小者矣。无如今为古人所愚,舍人参、熟地之奇,而必求首乌为延生变白之药,绝无一效,而不悔惑矣。
益母草益母草,味辛、甘,气微温。无毒。胎前、产后,皆可用之,去死胎最效,行瘀生新,亦能下乳。其名益母,有益于妇人不浅。然不佐之归、芎、参、术,单 味未能取胜。前人言其胎前无滞,产生无虚,谓其行中有补也。但益母草实非补物,止能佐补药以收功,故不宜多用。大约入诸补剂之中,以三钱为率,可从中再 减,断不可此外更增。
或问:益母草,以益母得名,宜其有益于产母。今人未产之前用之,犹曰治产母也,无孕之妇人杂然并进,益母之谓何?曰:益母草,实不止专益于产母,凡无产之 妇,均能受益。盖益线草治妇人之病,居十之七,治产母之病,反不过十之三。无产之妇,可以多用,而有产之妇,转宜少用耳。
或疑益母草古今共誉,而吾子何独有贬辞?曰:吾言益母草佐补药以收功。正显益母草之奇耳,何为贬辞哉?或疑益母草,古人单用以收功,而吾子必言佐补以取效,何也?不知益母草单用以收功,不若佐补收功之更多而且捷。
续断续断,味辛,气微温。无毒。善续筋骨,使断者复续得名。亦调血脉,疗折伤最神,治血症亦效。固精滑梦遗。暖子宫,补多于续,但不可多用耳。盖续断气 温,多用则生热,热生则火炽矣。少用则温而不热,肾水反得之而渐生。阴生于阳之中也。他本谓其能愈乳痈、瘰疬、肠风痔瘘,岂有气温之药,而能愈温热之病 乎?恐非可信之论也。
或问:续断能接筋骨。何以单用续断,未见奏功,入之于生血活血药中。反能奏效,何欤?曰:此正续断之奇也。夫断者不能复续,犹死者不能重生也。欲使断者复续,必须使死者重生矣。筋骨至于断,其中之血先死矣。
续断止能接筋骨之断,不能使血之生也。用之于生血、活血之中,则血之死者既庆再生,而筋骨之断者自庆再续。又何疑于单用之无功,而共用之甚效哉。
或疑续断不宜用之于补药之中。恐牵掣其手也。嗟乎。惟补可续,不补何续耶'。
或疑续断因补以接骨,则凡补之药,皆可接骨矣。曰:单补又何能接续哉。惟续断于补中接骨,则补即有生之义,生即有续之功也。
金银花金银花,一名忍冬藤。味甘,温,无毒。
入心、脾、肺、肝、肾五脏,无经不入,消毒之神品也。未成毒则散,已成毒则消,将死者可生,已坏者可转。故痈疽发背,必以此药为夺命之丹。但其味纯良,性 又补阴,虽善消毒,而功用甚缓,必须大用之。如发背痈,用至七八两,加入甘草五钱、当归二两,一剂煎饮,未有不立时消散者,其余身上、头上、足上各毒,减 一半投之,无不神效。近人治痈毒,亦多识用金银花,然断不敢用到半斤。殊不知背痈之毒。外虽小而内实大,非用此重剂,则毒不易消。且金银花少用则力单,多 用则力厚,尤妙在补先于攻,消毒而不耗气血,败毒之药,未有过于金银花者也。故毋论初起之时与出脓之后。或变生不测,无可再救之顷,皆以前方投之,断无不 起死回生者。正勿惊讶其药剂之重,妄生疑畏也。或嫌金银花太多,难于煎药,不妨先取水十余碗,煎取金银花之汁,再煎当归、甘草,则尤为得法。至于鬼击作 痛,又治之小者。止痢除温,益寿延龄,则不可为训矣。
或问:金银花败毒则有之,而吾子曰补阴,得毋惑于《本经》长年益寿之语乎?曰:金银花补之性实多于攻。攻毒之药,未有不散气者也,而金银花非惟不散气,且 能补气,更善补阴,但少用则补多于攻,多用则攻胜于补。故攻毒之药,未有善于金银花者也。若疑金银花为长年益寿之药,则不可。盖至纯之品,始可长服以延 龄,偏霸之味,止可暂投以奏效。金银花止宜用之以攻毒,而不宜用之以补虚。若惑于长年益寿之说,始信金银花为补阴之药,则余且劝人长服为添寿之助,何以止 言攻毒哉。
或问:金银花之解毒,近人亦多知之。然未有若吾子之赞叹甚神者,子欲显书之奇,不顾言之大乎?曰:金银花化毒,吾言止扬其十之五,余尚未尽言也。今因吾子 之问,而罄悉之。夫痈毒之初生也,其身必疼痛而欲死,服金银花,而痛不知何以消也;当痈毒之溃脓也,其头必昏眩而不能举,服金银花,而眩不知何以去也;及 痈毒之收口也,其口必黑黯而不能起,服金银花,而陷不知何以起也,然此犹阳症之痈毒也。若阴症之痈毒,其初生也.背必如山之重,服金银花,而背轻如释负 也;其溃脓也,心必如火之焚,服金银花,而心凉如饮浆也;其收口也,肉必如刀之割,服金银花,而皮痒如瓜搔也,然此犹阴症而无大变者也。倘若痛痒之未知, 昏愦之不觉,内可洞见其肺腑,而外无仅存之皮骨,与之食而不欲食,与之汤而不欲饮,悬性命于顷刻,候死亡于须臾,苟能用金银花一斤,同人参五、六两,共煎 汁饮之,无不夺魂于垂绝,返魄于已飞也。谁谓金银花非活人之仙草乎。其功实大,非吾言之大也。
或问:金银花散毒则有之,未必如是之神。曰:金银花之功效,实不止此。金银花无经不入,而其专入之经,尤在肾、胃二经。痈毒,止阴、阳之二种,阳即胃,而 阴即肾。阳变阴者,即胃之毒入于肾也;阴变阳者,即肾之毒入于胃也。消毒之品,非专泻阳明胃经之毒,即专泻少阴肾经之毒。欲既消胃毒,而又消肾毒之药,舍 金银花,实无第二品也。金银花消胃中之毒,必不使毒再入于肾脏,消肾中之毒,必不使毒重流于胃腑。盖金银花能先事而消弥,复能临事而攻突,更善终事而收敛 也。
或疑金银花性甚缓,而痈疽毒势最急,何以功用之大竟至如此,岂急症缓治之法欤?曰:痈疽势急,治法不啻救焚,乌可以缓治之哉。金银花性缓,而用之治痈疽也,则缓而变为急矣,况用之四、五两,以至半斤、一斤,则其力更专,而气更勇猛,此正急症急治之也。
巴戟天巴戟天,味甘、温,无毒。入心、肾二经。
补虚损劳伤,壮阳道,止小腹牵痛,健骨强筋,定心气,益精增志,能止梦遗。此臣药,男妇俱有益,不止利男人也。世人谓其能使痿阳重起,故云止利男子。不知 阳事之痿者,由于命门火衷,妇人命门与男子相同,安在不可同补乎。夫命门火衰,则脾胃寒虚,即不能大进饮食,用附子、肉桂,以温命门,未免过于太热,何如 用巴戟天之甘温,补其火,而不烁其水之为妙耶。
或问:巴戟天近人罕用,止用之于丸散之中,不识亦可用于汤剂中耶?曰:巴戟天,正汤剂之妙药,无如近人不识也。巴戟天,温而不热,健脾开胃,既益元阳,复 填阴水,真接续之利器,有近效,而又有远功。夫巴戟天虽入心、肾,而不入脾、胃,然入心,则必生脾胃之气,故脾胃受其益。汤剂用之,其效易速,必开胃气, 多能加餐,及至多餐,而脾乃善消。
又因肾气之补,薰蒸脾胃之气也,谁谓巴戟天不宜入于汤剂哉。
巴戟天温补命门,又大补肾水,实资生之妙药。单用一味为丸,更能补精种子,世人未知也。
或疑巴戟天入汤剂最妙,何以前人未见用之?曰:前人多用,子未知之耳。夫巴戟天,补水火之不足,益心肾之有余,实补药之翘楚也。用之补气中,可以健脾以开 胃气;用之补血之中,可以润肝以养肺阴,古人不特用之,且重用之,自黄柏、知母之论兴,遂置巴戟天于无用之地。嗟乎!人生于火,而不生于寒,如巴戟天之 药,又乌可不亟为表扬哉。
五加皮五加皮,味辛而苦,气温而寒,无毒。近人多取而酿酒,谓其有利益也,甚则夸大其辞,分青、黄、赤、白、黑,配五行立论,服三年可作神仙,真无稽之谈也。此物止利风湿,善消瘀血则真。若言其扶阳起痿,止小便遗沥。
去妇人阴痒,绝无一验。而举世宗之,牢不可破,亦从前著书者之误也。余故辨之,使世人毋再惑耳。
或问:五加皮,举世皆以为补,先生独言非补,世人饮此酒未见有损,何也?曰:有其功则言功,有其弊而言弊。五加皮,实有损无益之药,而举世宗之,余所以大声疾呼也。此酒江淮之间最多,然饮之而未见损者,亦有其故。盖江淮地势卑湿,服五加皮之酒以去湿,似乎得宜。若非江淮污下之所,而地处高燥,则燥以益燥,吾日见其损,而不见其益矣。
或问:东华真人煮石法用五加皮,世为仙经所需,而昔年鲁定公母单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岂皆不可信耶?曰:此皆造酒附会之辞也。五加皮实止除湿,而不能延年,欲藉其轻身耐老,此余之所不敢信也。
川芎川芎,味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厥阴二经。功专补血。治头痛有神,行血海,通肝经之脏,破瘙结宿血,产后去旧生新,凡吐血、衄血、溺 血、便血、崩血,俱能治之。血闭者能通,外感者能散,疗头风甚神,止金疮疼痛。此药可君可臣,又可为佐使,但不可单用,必须以补气、补血之药佐之,则利大 而功倍。倘单用一味以补血,则血动,反有散失之忧;单用一味以止痛,则痛止,转有暴亡之虑。若与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同用以补气,未必不补气以生血也; 若与当归、熟地、山茱、麦冬、白芍以补血,未必不生血以生精也。所虞者,同风药并用耳,可暂而不可常,中病则已,又何必久任或。
或问:川芎既散真气,用四物汤以治痨怯,毋乃不可乎?不知四物汤中,有当归、熟地为君,又有芍药为臣,用川芎不过佐使,引入肝经,又何碍乎?倘四物汤,减去川芎,转无效验。盖熟地性滞,而芍药性收,正藉川芎辛散以动之也。又未可鉴暴亡之失,尽去之以治虚劳也。
或问:佛手散用川芎,佐当归生血,为产门要药,我疑其性动而太散,何以产后之症偏服之,而生血且生气也?夫血不宜动,而产后之血,又惟恐其不动也。产后之血一不动,即凝滞而上冲,则血晕之症生矣。佛手散,正妙在于动也,动则血活,旧血易去,而新血易生。
新血既生,则新气亦自易长,又何疑川芎性动而太散哉。
或问:川芎散气是真,何以补血药必须用之,岂散气即生血.乎?曰:血生于气,气散则血从何生。不知川芎散气,而复能生血者,非生于散,乃生于动也。血大 动,则走而不能生;血不动,则止而不能生矣。川芎之生血,妙在于动也。单用一味,或恐过动而生变,合用川芎,何虞过动哉。所以为生血药中之必需,取其同群 而共济也。
或问:川芎妙在于动而生血,听其动可也。胡必用药以佐之,使动而不动耶?不知动则变者,古今之通义。防其变者,用药之机权。川芎得群补药,而制其动者,正 防其变也。虽然,天下不动则不变,不制其动而自动者,必生意外之变,其变为可忧;制其动而自动者,实为意中之变,其变为可喜。盖变出意外者,散气而使人暴 亡;变出意中者,生血而使人健旺。血非动不变,血非变不化也。
或疑川芎生血出于动,又虑其生变而制其动,则动犹不动也,何以生血之神哉?曰:不动而变者,无为而化也。川芎过动,而使之不动,则自忘其动矣。其生血化血,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是不动之动,正治于动也。
或疑川芎生血而不生气,予独以为不然。
盖川芎亦生气之药,但长于生血,而短于生气耳。世人见其生血有余,而补气不足,又见(神家本草》言其是补血之药,遂信川芎止补血,而不生气,绝无有用补气 之中。岂特无有用之于补气,且言耗气而相戒。此川芎生气之功,数千年未彰矣,谁则知川芎之能生气乎。然而川芎生气,实不能自生也,必须佐参、术以建功,辅 芪、归以奏效,不可嫌其散气而不用之也。
或疑川芎生气,终是创谈,仍藉参、术、芪、归之力,未闻其自能生气也。曰:用川芎,欲其自生气也,固力所甚难;用川芎,欲其同生气也,又热所甚易。盖川芎 得参、术、芪、归,往往生气于须臾,生血于眉睫,世人以为是参、术、芪、归之功也。然何以古人不用他药以佐参、术、芪、归,而必用川芎以佐之,不可以悟生 气之说哉。
或疑川芎用之于佛手散中,多获奇功,离当归用之,往往愤事,岂川芎与当归,性味之相宜耶?夫当归性动,而川芎亦动,动与动相合,必有同心之好,毋怪其相得益彰也。然而两动相合,反不全动,故不走血,而反生血耳。
或问:川芎性散而能补,是补在于散也。
补在散,则补非大补,而散为大散矣。不知散中有补,则散非全散。用之于胎产最宜者,盖产后最宜补,又虑过补则血反不散,转不得补之益矣。川芎于散中能补,既无瘀血之忧。又有生血之益,妙不在补而在散也。
芍药芍药、昧苦、酸,气平、微寒,可升可降,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又入厥阴、少阳之经。能泻能散,能补能收,赤自相,无分彼此。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而脏腑各安,大小便自利,火热自散,郁气自除,痈肿自消,坚积自化,泻痢自去,痢痛自安矣。
盖善用之,无往不宜,不善用之,亦无大害。
无如世人畏用,恐其过于酸收,引邪入内也。
此不求芍药之功,惟求芍药之过。所以,黄农之学,不彰于天下,而夭札之病,世世难免也,予不得不出而辨之。夫人死于疾病者,色欲居其半,气郁居其半。纵色 欲者,肝经之血必亏,血亏则木无血养,木必生火,以克脾胃之土矣。脾胃一伤,则肺金受刑,何能制肝。木寡于畏,而仍来克土,治法必须滋肝以平木。
而滋肝平木之药,舍芍药之酸收,又何济乎。
犯气郁者,其平日肾经之水,原未必大足以生肝木,一时又遇拂抑,则肝气必伤。夫肝属木,喜扬而不喜抑者也,今既拂抑而不舒,亦必下克于脾土,脾土求救于肺 金,而肺金因肝木之旺,肾水正亏,欲顾子以生水,正不能去克肝以制木,而木气又因拂抑之来,更添恼怒,何日是坦怀之日乎。治法必须解肝木之忧郁,肝舒而脾 胃自舒,脾胃舒,而各经皆舒也。舍芍药之酸,又何物可以舒肝乎。是肝肾两伤,必有资于芍药,亦明矣。然而芍药少用之,往往难于奏效。盖肝木恶急,遽以酸收 少济之,则肝木愈急,而木旺者不能平,肝郁者不能解。必用至五、六钱,或八钱,或一两,大滋其肝中之血,始足以慰其心而快其意,而后虚者不虚,郁者不郁 也。然则芍药之功用,如此神奇,而可以酸收置之乎。况芍药功用,又不止二者也,与当归并用,治痢甚效;与甘草并用,止痛实神;与栀子并用,胁痛可解;与蒺 藜并用,目疾可明,且也与肉桂并用,则可以祛寒;与黄芩并用,则可以解热;与参、芪并用,则可以益气;与芎、归、熟地并用,则可以补血。用之补则补,用之 泻则泻,用之散则散,用之收则收,要在人善用之,乌得以酸收二字而轻置之哉。
或问:芍药有不可用之时,先生之论,似乎无不可用,得毋产后亦可用,而伤寒传经亦可用乎?曰:产后忌芍药者,恐其引寒气入腹也,断不可轻用。即遇必用芍药 之病,止可少加数分而已。若伤寒未传太阳之前,能用芍药,则邪尤易出。惟传入阳明,则断乎不可用。至于入少阳、厥阴之经,正须用芍药和解,岂特可用而已 哉。
或问:芍药平肝气也,肝气不逆,何庸芍药,吾子谓芍药无不可用,毋乃过于好奇乎?夫人生斯世,酒、色、财、气,四者并用,何日非使气之日乎。气一动,则伤 肝,而气不能平矣。气不平,有大、小之分,大不平。则气逆自大;小不平,则气逆亦小。人见气逆之小,以为吾气未尝不平也,谁知肝经之气已逆乎。
故平肝之药,无日不可用也,然则芍药又何日不可用哉。
或问:郁症利用芍药,亦可多用之乎?曰:芍药不多用,则郁结之气,断不能开。世人用香附以解郁,而郁益甚,一多用芍药,其郁立解,其故何也?盖郁气虽成于 心境之拂抑,亦终因于肝气之不足,而郁气乃得而结也。用芍药以利其肝气,肝气利,而郁气亦舒。但肝因郁气之结,则虚者益虚,非大用芍药以利之,则肝气未易 复,而郁气亦未易解也。故芍药必须宜多用以平肝,而断不可少用以解郁耳。
或问:芍药虽是平肝,其实乃益肝也。益肝则肝木过旺,不畏肝木之克土乎?目:肝木克土者,乃肝木之过旺也。肝木过旺则克土,肝木既平,何至克土乎。因肝木 之过旺而平肝,则肝平而土已得养。土得养,则土且自旺,脾胃既有旺气,又何畏于肝木之旺哉。况肝木因平而旺,自异于不平而自旺也。不平而自旺者,土之所 畏;因平而旺者,土之所喜。
盖木旺而土亦旺,土木有相得之庆,又何畏于肝木之克哉。
或问:芍药妙义,先生阐发无遗,不识更有异闻,以开予之心胸乎?曰:芍药之义,乌能一言而尽哉,但不知吾子欲问者。用芍药治何经之病也,或人以克胃者,何以用芍药耶。夫芍药平肝,而不平胃,胃受肝木之克,泻肝而胃自平矣,何必疑。
或又曰:非此之谓也。余所疑者,胃火炽甚,正宜泻肝木,以泻胃火,何以反用芍药益肝以生木,便木旺而火益旺耶?目:胃火之盛,正胃土之衰也。胃土既衰,而肝木又旺,宜乎克土矣。谁知肝木之旺,乃肝木之衰乎。
肝中无血则干燥,而肝木欲取给于胃中之水以自养,而胃土之水,尽为木耗,水尽则火炽,又何疑乎。用芍药以益肝中之血,则肝足以自养其木,自不至取给于胃中 之水,胃水不干,则胃火自息,山下出泉,不可以济燎原之火乎。此盖肝正所以益胃也。或人谢曰:先生奇论无穷,不敢再难矣。
或又问曰:肝木之旺,乃肝木之衰,自当用芍药以益肝矣,不识肝木不衰,何以亦用芍药:曰:子何以见肝木之不衰也。或人目:胁痛而至手不可按,目疼而至日不可见,怒气而血吐之不可遏,非皆肝木之大旺而非衰乎。
嗟乎!子以为旺,而我以为衰也。夫胁痛至手不可按,非肝血之旺,乃肝火之旺也,火旺由于血虚;目痛至日不可见,非肝气之旺,乃肝风之旺也,风旺由于气虚怒 极;至血之狂吐,非肝中之气血旺也,乃外来之事,触动其气,而不能泄,使血不能藏而外越,然亦因其平日之肝木素虚,而气乃一时不能平也。三症皆宜用芍药以 滋肝,则肝火可清,肝风可去,肝气可舒,肝血可止。否则,错认为旺,而用泻肝之味,变症蜂起矣。总之,芍药毋论肝之衰旺、虚实,皆宜必用,不特必用,而更 宜多用也。
或又问曰:肝虚益脾,敬闻命矣,何以心虚而必用芍药耶?夫肝为心之母,而心为肝之子也,子母相关,补肝正所以补心,乌可弃芍药哉。或人曰:予意不然。以心为君主之官,心虚,宜五脏兼补,何待补肝以益心哉。
嗟乎!补肾可以益心,必不能舍肝木而上越;补脾可以益心,必不能外肝木而旁亲;补肺可以益心,亦不能舍肝木而下降。盖肾交心,必先补肝,而后肾之气始可交 于心之中,否则,肝取肾之气,而心不得肾之益矣。脾滋心,必先补肝,而后脾之气,始足滋于心之内,否则,肝盗脾之气,而心不得脾之益矣。肺润心,必先补 肝,而后肺之气,始得润于心之宫,否则,肝耗肺之气,而心不得肺之益矣。可见肾、脾、肺三经之入心,俱必得肝气而后入,正因其子母之相亲,他脏不得而间之 也。三脏补心,既必由于肝,而肝经之药,何能舍芍药哉。
非芍药不可补肝以补心,又何能舍芍药哉。
或问:芍药平肝之药也,乃有时用之以平肝,而肝气愈旺,何故乎?曰:此肺气之衰也。
肺旺,则肝气自平,金能克木也。今肝旺之极,乃肺金之气衰极也,不助金以生肺,反助木以生肝,则肝愈旺矣,何畏弱金之制哉,此用芍药而不能平肝之义也。
或问:芍药不可助肝气之旺,敬闻命矣。
然有肝弱而用之,仍不效者,又是何故?此又肺气之过旺也。肝弱补肝,自是通义。用芍药之益肝,谁日不宜。然而肝之所畏者,肺金也,肺气大旺,则肝木凋零。 用芍药以生肝气,而肺金辄来伐之,童山之萌芽,曷胜斧斤之旦旦乎。故芍药未尝不生肝经之木,无如其生之而不得也。必须制肺金之有余,而后用芍药以益肝木之 不足。樵采不入于山林,枝叶自扶苏于树木,此必然之势也,又何疑于芍药之不生肝木哉?或问:芍药生心,能之乎?夫心乃肝之子也,肝生心,而芍药生肝之物, 独不可生肝以生心乎。独是生肝者,则直入于肝中,而生心者,乃旁通于心外,毕竟入肝易,而入心难也。
虽然,心乃君主之宫,补心之药不能直入于心宫,补肝气,正所以补心气也。母家不贫,而子舍有空乏者乎。即有空乏,可取之于母家而有余。然则芍药之生心,又不必直入于心中也。
或疑芍药味酸以泻肝,吾子谓是平肝之药,甚则誉之为益肝之品,此仆所未明也。嗟乎?肝气有余则泻之,肝气不足则补之。
平肝者,正补泻之得宜,无使不足,无使有余之谓也。芍药最善平肝,是补泻攸宜也。余言平肝,而泻在其中矣,又何必再言泻哉?或疑芍药赤、白有分,而先生无 分赤、白,又何所据而云然哉。无芍药之不分赤、白,非创说也,前人已先言之矣。且世人更有以酒炒之者,皆不知芍药之妙也。夫芍药正取其寒,以凉肝之热,奈 何以酒制,而使之温耶。
既恐白芍之凉,益宜用赤芍之温矣,何以世又尚白而尚赤也?总之,不知芍药之功用,而妄为好恶,不用赤而用白,不用生而用熟也,不大可晒也哉。
黄芩黄芩、味苦,气平,性寒,可升可降,阴中微阳,无毒。入肺经、大肠。退热除烦,泻膀胱之火.止赤痢,消赤眼,善安胎气,解伤寒郁蒸,润燥,益肺气。但 可为臣使,而不可为君药。近人最喜用之,然亦必肺与大肠、膀胱之有火者者,用之始宜,否则,不可频用也。古人云黄芩乃安胎之圣药,亦因胎中有火,故用之于 白术、归身、人参、熟地、杜仲之中,自然胎安。倘无火,而寒虚胎动,正恐得黄芩而反助其寒,虽有参、归等药补气、补血、补阴,未必胎气之能固也。况不用 参、归等药,欲望其安胎,万无是理矣。
或问:黄芩清肺之品也,肺经之热,必须用之,然亦有肺热用黄芩而转甚者,何也?曰:用黄芩以清肺热,此正治之法也。正治者,治肺经之实邪也。肺经有实邪,黄芩用之,可以解热;肺经有虚邪,黄芩用之,反足以增寒。盖实邪宜正治,而虚邪宜从治也。
或问:黄芩举世用而无疑,与用知母、黄柏颇相同,乃先生止咎用知母、黄柏之误,而不咎用黄芩,何也?曰:黄芩亦非可久用之药.然其性寒而不大甚,但入于 肺,而不入于肾。世人上热多,而下热者实少,清上热,正所以救下寒也。虽多用久用,亦有损于胃,然肾经未伤,本实不拨,一用温补,便易还原,其弊尚不至于 杀人。若知母、黄柏泻肾中之火矣,肾火消亡,脾胃必无生气,下愈寒而上愈热,本欲救阴虚火动,认谁知反愈增其火哉。
下火无根,上火必灭,欲不成阴寒世界得乎。
此用黄柏、知母之必宜辟也。
或问:黄芩乃清肺之药,肺气热,则肾水不能生,用黄芩以清肺金,正所以生肾水乎?曰:黄芩但能清肺中之金,安能生肾中之水。
夫肺虽为肾经之母,肺处于上游,居高润下,理之常也,何以清金而不能生水。盖肺中之火乃邪火,而非真火也,黄芩止清肺之邪火耳,邪火散而真水自生,安在不可下生肾水。
不知肾水之生,必得真火之养,黄芩能泻邪火,而不能生真火,此所以不能生肾水也。予之取黄芩者,取者暂用以全金,非取其久用以益水。
或疑黄芩之寒凉,不及黄柏、知母,以黄芩味轻,而性又善散,吾子攻黄柏、知母宜也,并及黄芩,毋乃过乎?曰:黄芩之多用,祸不及黄柏、知母远甚,余未尝有 过责之辞,独是攻击知母、黄柏,在于黄芩门下而畅论之,似乎并及黄芩矣。谁知借黄芩以论黄柏、知母,意重在黄柏、知母也。见黄芩之不宜多用,益知黄柏、知 母,意重在黄柏、知母也。见黄芩之不宜多用,益知黄柏,知母之不可重用矣。
世重寒凉,病深肺脏,不如此,又何以救援哉。
黄连黄连,味苦,寒,可升可降,阴也,无毒。
入心与胞络。最泻火,亦能入肝。大约同引经之药,俱能入之,而入心,尤专经也。止吐利吞酸,善解口渴。治火眼甚神,能安心,止梦遗,定狂躁,除痞满,去妇 人阴户作肿。治小儿食土作疳,解暑热、湿热、郁热,实有专功。但亦臣使之药,而不可以为君,宜少用而不宜多用,可治实热而不可治虚热也。盖虚火宜补,则实 火宜泻。以黄连泻火者,正治也;以肉桂治火者,从治也。故黄连、肉桂,寒热实相反,似乎不可并用,而实有并用而成功者。盖黄连入心,肉桂入肾也。凡人日夜 之间,必心肾两交,而后水火始得既济,火水两分,而心肾不交矣。心不交于肾,则日不能寐;肾不交于心,则夜不能寐矣。黄连与肉桂同用,则心肾交于顷刻,又 何梦之不安乎。
或问:苦先入心,火必就燥,黄连味苦而性燥,正与心相同,似乎入心之相宜矣,何以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不解心热,而反增其焰者,何也?臼:此正见用黄连之 宜少,而不宜多也。盖心虽属火,必得肾水以相济,用黄连而不能解火热者,原不可再泻火也。火旺则水益衰,水衰则火益烈,不下治而上治,则愈增其焰矣。譬如 釜内无水,止成焦釜,以水投之,则热势上冲而沸腾矣。治法当去其釜下之薪,则釜自寒矣。故正治心火而反热者,必从治心火之为安,而从治心火者,又不若大补 肾水之为得。盖火得火而益炎,火得水而自息耳。
或问:黄连止痢而厚肠胃,吾子略而不谈,何也?曰:此从前《本草》各书,无不载之,无俟再言也。然而予之不谈者,叉自有在。
盖黄连非治痢之物,泻火之品也。痢疾湿热,用黄连性燥而凉。以解湿而除热似矣。殊不知黄连独用以治痢,而痢益甚,用之于人参之中,治噤口之痢最神;用之于 白芍、当归之中,治红赤之痢最效,可借之以泻火,而非用之以止痢,予所以但言其泻火耳。况上文曾言止吐利吞酸,利即痢也,又未尝不合言之矣。至于厚肠胃之 说,说者谓泻利日久,下多亡阴,刮去脂膜,肠'胃必薄矣,黄连既止泻利,则肠胃之薄者,可以重厚。嗟乎!此臆度之语,而非洞垣之说也。夫黄连性燥而寒凉, 可以暂用,而不可久用。肠胃之脂膜既伤,安得一时遽厚哉。夫胃薄者,由于气血之衰,而肠薄者,由于精水之耗。黄连但能泻火,而不能生气血、精水,吾不知所 谓厚者,何以厚也。
或问:黄连泻火,何以谓之益心,可见寒凉未必皆是泻药。曰:夫君之论,是欲扬黄柏、知母也。吾闻正寒益心,未闻正寒益肾。
夫心中之火,君火也;肾中之火,相火也。正寒益心中之君火,而益心中之相火。虽心中君火,每藉心外相火以用事,然而心之君火则喜寒,心之相火则喜热。以黄 连治心之君火,则热变为寒;以黄连治心之相火,则寒变为热。盖君火宜正治,而相火宜从治也。夫相火在心火之中,尚不用寒以治热,况相火在肾水之内,又乌可 用寒以治寒乎。昔丹溪用黄柏、知母,入于六味丸中,未必不鉴正寒益心,亦可用正寒以益肾也。谁知火不可以水灭,肾不可与心并论哉。
或疑世人用黄连,不比用黄柏、知母,先生辟黄柏、知母,何必于论黄连之后,而大张其文澜哉?嗟乎!是有说焉,不可不辨也。
夫人生于火,不闻生于寒也。以泻火为生,必变生为死矣。从来脾胃喜温,而不喜寒,用寒凉降火,虽降肾火也,然胃为肾之关门,肾寒则胃寒,胃寒则脾亦寒。脾胃既寒,又何以蒸腐水谷哉。下不能消,则上必至于不能受,上下交困,不死何待乎。
又肺金之气,必夜归于肾之中,肾火沸腾,则肺气不能归矣。然补其肾水,而益其肺金,则肾足,而肺气可复归于肾。倘肾寒则肾火不归,势必上腾于肺,而又因肾 之寒,不敢归于下,则肺且变热,而咳嗽之症生。肺热而肾寒,不死又何待乎。慨自虚火实火、正火邪火、君火相火之不明,所以治火之错也。夫黄连,泻实火也, 补正火也,安君火也,不先将黄连之义,罄加阐扬,则虚火、邪火、相火之道,终不明于天下。吾所以于黄连门中,痛攻黄柏、知母,使天下后世知治火之药,不可 乱用寒凉,实救其源也。
桔梗桔梗,味苦,气微温,阳中阴也,有小毒。
入手足肺、胆二经。润胸膈,除上气壅闭,清头目,散表寒邪,祛胁下刺痛,通鼻中窒塞,治咽候肿痛,消肺热有神,消肺痈殊效,能消恚怒,真舟楫之需,引诸药 上升,解小儿惊痫,提男子血气,为药中必用之品,而不可多用者也。盖少用,则攻补之药,恃之上行以去病;多用,则攻补之药,借之上行而生殃。惟咽喉疼痛, 与甘草多用,可以立时解氛,余则戒多用也。
或问:桔梗乃舟楫之需,毋论攻补之药,俱宜载之而上行矣,然亦不能载之者,何故?曰:桔梗之性上行,安有不能载之者乎。其不能载者,必用药之误也。夫桔梗上行之药,用下行之药于攻补之中,则桔梗欲上而不能上。
势必下行之药,欲下而不能下矣。余犹记在襄武先辈余叔岩,闻余论医,阴虚者宜用六味地黄汤,阳虚者宜用补中益气汤。徐君曰:余正阴阳两虚也。余劝其夜服地 黄汤,日服补中益气汤,服旬日,而精神健旺矣。别二年复聚,惊其精神不复似昔,问曾服前二汤否,徐君曰:子以二汤治予病,得愈后,因客中无仆,不能朝夕煎 饮消息子之二方,而合为丸服,后气闭于胸膈之间,医者俱言二方之不可长服,予久谢绝。今幸再晤,幸为我治之。予仍以前二方,令其朝夕分服,精神如旧。徐君 曰:何药经吾子之手,而病即去也,非夫医而何?余曰:非余之能,君自误耳。徐问故。余曰:六味地黄汤,补阴精之药,下降者也;补中益气汤,补阳气之药,上 升者也。二汤分早晚服之,使两不相妨,而两有益也。今君合而为一,则阳欲升,阴又欲降,彼此势均力敌,两相持,而两无升降,所以饱闷于中焦,不上不下也。 徐君谢曰:医道之渊微也如此。夫桔梗与升麻、柴胡,同是升举之味,而升麻、柴胡用之于六味汤丸之内,其不能升举如此,然则桔梗之不能载药上行,又何独不然 哉。正可比类而共观也。
或问:桔梗散邪,而不耗正气,何以戒多用也?曰:桔梗亦有多用而成功。少阴风邪,致喉痛如破者,多用之而邪散如响。是邪在上者,宜多用;而邪在下者,即不宜多用。
或问:《古今录验方》中载桔梗治中蛊毒,下血如鸡肝片者血块石余,服方寸匕,七日三服而愈,其信然乎?曰:此失其治蛊之神方,止记其引导之昧也。中蛊必须 消毒,下血必须生血,一定之理也。桔梗既非消毒之品。又非生血之药,乌能治蛊而止血乎。盖当时必有神奇之丸,以酒调化,同桔梗汤送之奏功,而误传为桔梗, 《古今录》遂志之也。
或问:桔梗不可多用,而吾子又谓可以多用,何言之相背也?曰:邪在上者宜多,邪在下者宜少,余已先辨之,未尝相背也。
虽然,用药贵得其宜,要在临症斟酌。有邪在上。多用桔梗而转甚;有邪在下,少用桔梗而更危。
盖邪有虚实之不同,而桔梗非多寡之可定,故实邪可用桔梗,而虚邪断不可用桔梗也。
栝蒌实附天花粉栝萎实,味苦,气寒,降也,阴也,无毒。
入肺、胃二经。最能下气涤秽,尤消郁开胃,能治伤寒结胸,祛痰,又解渴生滓,下乳。但切戒轻用,必积秽滞气结在胸上,而不肯不者,始可用之以荡涤,否则,万万不可孟浪。
盖栝蒌实最消人之真气,伤寒结胸,乃不得已用之也。苟无结胸之症,何可轻用。至于消痰、解渴、下乳,止可少少用之,亦戒不可重任。他本言其能治虚怯劳嗽,此杀人语,断不可信,总惑于补肺之说也。夫栝蒌乃攻坚之药,非补虚之品。
天花粉,即栝蒌之根,而性各不同。盖栝蒌实其性最悍,非比天花粉之缓,用栝萎实,不若以天花粉代之。天花粉,亦消痰降气,润渴生津,清热除烦,排脓去毒,逐瘀定狂,利小便而通月水。其功用多于栝萎实,虚人有痰者,亦可少用以解燥而滋枯,又何必轻用栝萎实哉。
或问:栝萎实能陷胸中之邪,为伤寒要药,而吾子切切戒之,何不删去栝蒌,独存天花粉之为哉?曰:医道必王、霸并用,而后出奇制胜,始能救生死于顷刻。结胸 之症,正死在须臾也,用天花粉以消痞满,其功迟,用栝楼以消痞满,其功捷。但结胸之痞满不同,小痞小满之症,不妨用天花粉以消之;大痞大满之症,非栝蒌断 然不可。又在人临症细辨,非栝蒌之竟可不用也。
或疑栝萎推胸中之食,荡胃中之邪,其势甚猛。伤寒至结胸,其正气已大丧矣,又用此以推荡之,不虚其虚乎?先生又谓不可用天花粉相代,岂伤寒之虚,可以肆然不顾乎?曰:伤寒不顾其虚,则邪且铄尽人之元气,顷刻即死矣,乌可肆然不顾乎。用栝蒌以陷胸,正所以顾其虚也。夫陷胸之成,由于邪退之时,而亟用饮食,则邪仍聚而不肯散。夫邪之所以散者,由于胃中空虚, 邪无所得,故有不攻而散之意。邪甫离胃,而胃气自开,以致饥而索食,此时而能坚忍半日,则邪散尽矣。无如邪将散,而人即索食,食甫下喉,而邪复群聚而逐 矣。仲景张夫子所以又立陷胸汤,用栝蒌为君,突围而出,所向无前,群邪惊畏,尽皆退舍,于是,渐次调补,而胸胃之气安焉。
是推荡其邪气,非即急救其正气之明验乎。
倘畏首畏尾,不敢轻用栝蒌,虽久则食消,亦可化有事为无事。然所伤正气多矣,此栝蒌之宜急用,而不可失之观望耳。
或问:栝萎陷胸,以救胃中之正气是矣,然吾恐栝萎祛邪以入脾,走而不守,则脾当其害,不犹以邻国为壑乎?曰:栝蒌但能陷胸,而不能陷腹。胸中之食,可推之以入于腹,脾中之食,不必荡之以入于肠。盖脾主出而易化,胃主纳而难消也。
或问:栝蒌陷胸中之邪,抑陷胸中之食耶?曰:结胸之症,未有不因食而结者也。陷胸汤乃陷食,而非陷邪也。虽然,邪因食而复聚,虽邪不入于胃之中,而邪实布于胃之口。
陷胸中之食而邪解散,即谓之陷邪亦可也。
然而食可陷,而邪不可陷。食陷必入于肄,邪陷必入于肾。入脾者,栝蒌可乘胜而长驱,入肾者,栝萎不能入肾,势必变生不测。今用陷胸,而食消邪散,是陷胸汤实陷食,而非陷邪也。但止陷食而不陷邪,而邪何以竟散耶?是结胸之症因得食而结,则陷胸之汤,其邪亦因陷食而散也。
或疑陷胸汤用栝蒌,不止陷胸中之邪,亦陷腹中之邪也,邪在腹中,安知不祛之入肾乎?曰:陷胸汤势最捷。邪逢栝萎即散,安在又入于肾乎。况邪已在腹,与在胸者有别,在胸者,居高临下,恐有走失入肾之虞;在腹者,邪趋大肠,其势甚便,岂返走于肾经哉。
或问:栝蒌与天花粉。同为一本,何以天花粉反不似栝蒌之迅扫胸中之邪耶。曰:天花粉消痞满,其功缓;栝蒌实消痞满,其功捷,余前条已言,但未言其所以缓与 捷也。夫栝蒌为天花粉之子,而天花粉为栝蒌之根.子悬于天下,而性实顾根,故趋于下者甚急;根藏于地中,而性实恋子,故育于上者自缓。缓捷之故,分于此, 而陷消之功,亦别于此。故宜缓者用天花粉,宜急者用栝萎实,又何虑功效之不奏哉。
紫菀紫菀,味苦、辛,温,无毒。入手太阴,兼入足阳明。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去蛊毒,疗咳唾脓血,止喘悸、五劳体虚,治久嗽。
然亦止可为佐使,而不可单用以取效。、或问:缪仲醇云:观紫菀能开喉痹,取恶涎,则辛散之功烈矣。然而又云:其性温,肺病咳逆喘嗽,皆阴虚肺热症也,不宜 多用等语,似乎紫菀并不可以治嗽也。曰:紫菀舍治嗽之外,原无多奇功。治缠喉风、喉闭者,正取其治肺经咳逆、阴虚肺热也,而仲醇以此相戒,何哉。夫喉闭, 未有非下寒上热之症也。
紫菀性温,而又兼辛散,从其火热之性而解之,乃从治之法,治之最巧者也。仲醇最讲阴虚火动之旨,何独于紫苑而昧之,此铎所不解也。
或谓:紫苑治肺之热,而性温而辛散,从火热之性而解之是矣。然而肺经最恶热,以热攻热,必伤肺矣。吾恐邪去而肺伤也。
曰:久嗽则肺必寒。以温治寒,则肺且受益,何伤之有。
贝母贝母,味苦,气平、微寒,无毒。入肺、胃、脾、心四经。消热痰最利,止久嗽宜用,心中逆气多愁郁者可解。并治伤寒结胸之症,疗人面疮能效。难产与胞衣 不下,调服于人参汤中最神。黄瘅赤眼,消渴除烦,喉痹,疝瘕,皆可佐使,但少用足以成功,多用或以取败。宜于阴虚火盛,不宜于阳旺湿痰。世人不知贝母与半 夏,性各不同,惧半夏之毒。每改用贝母。不知贝母消热痰,而不能消寒痰,半夏消寒痰,而不能消热痰也,故贝母逢寒痰。则愈增其寒;半夏逢热痰,则大添其 热。二品泾胃各殊,乌可代用,。前人辨贝母入肺,而不入胃,半夏入脾胃,而不入肺经,尚不知贝母之深也。盖贝母入肺、胃、脾、心四经,岂有不入脾、胃之理 哉。正寒热之不相宜,故不可代用也。
或问:贝母之疗人面疮,可信不可信乎?曰:此前人之成效,胡必疑之。然而有可疑者。人面疮,口能食而面能愁,盖有祟凭之矣。祟凭必须解祟,何以用贝母即 解,予久不得其故。后遇岐天师于燕市,另传治法,而后悟贝母之疗人面疮也。亦消其痰而已矣。夫怪病多起于痰,贝母消痰,故能愈也。如半夏亦消痰圣药,何治 人面疮无效?不知人面疮,乃热痰结成热毒,半夏性燥,燥以治热,更添热矣。贝母乃治热痰圣药,以寒治热,而热毒自消,又何疑哉。
或问:贝母消痰,消热痰也,然火沸为痰,非热乎,何以用之而绝无效耶?曰:火沸生痰,乃肾中之火上沸,非肺中之火上升。贝母止可治肺中之火痰,不化肾中之 火痰也。岂惟不能化肾中之火痰,且动火而生痰矣。夫肾中之火,非补水不能除,肾火之痰,亦非补水不能消。贝母消肺中之痰,心铄肺中之气,肺虚则肾水之化源 竭矣,何以生肾水哉。肾水不生,则肾火不降。
肾火不降,又何以健脾而消痰哉。势必所用水谷不化精而化痰矣。
然则用贝母以治火沸为痰,不犹添薪而望止沸乎。毋怪沓无功效也。
或疑贝母不可治火沸为痰之症,吾用之六味丸中,亦可以治之乎?曰:六味汤止治火沸为痰之圣药也,加入贝母,则不效矣。
盖火沸为痰,乃肾中之真水上沸而成痰,非肺中之津液上存而为痰也。六味汤补水以止沸,非化痰以止火。倘加入贝母,则六味欲趋于肾中,而贝母又欲留于肺内, 两相牵掣,则药必停于不上不下之间。痰既不消,火又大炽,不更益其沸,而转添其咳嗽哉。此贝母断不可入于六味汤丸之中。治火沸为痰之病也。
款冬花款冬花。辛、甘而温,阳也,无毒。善止肺咳,消痰唾稠粘,润肺,泻火邪,下气定喘,安心惊胆怯,去邪热,除烦燥,平肝明目。烧烟吸之,亦善止嗽,尤 能止肺咳肝嗽。近人喜用紫菀,而不用款冬者,殊不可解。紫菀虽亦止久嗽,而味苦伤胃,不若款冬之味甘,清中有补也。余所以取款冬而弃紫菀耳。
或问:款冬花.清中有补,多用之以益肺、益肝、益心可乎?曰:款冬花虽清中有补,而多用亦复不宜,盖补少而清多也。夫款冬花入心则安心,入肝则明目,入肺 则止咳,是其补也。然入心,则又泻心之火,多用则心火过衰,反不生胃以健食矣;入肝,则又泻肝之气,多用则心火过凋,反不能生心以定神矣;入肺,则又泻肺 之气,多用则肾气过寒,反不能生脾以化物矣。
是款冬花多用则伤,少用则益,又何必多用哉。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