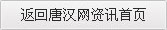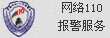殖民医学下的卫生意识冲突与妥协—以清末上海地区为例
核心提示: 殖民医学指发生在任何殖民地的任何医学实践,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殖民文化基础的
殖民医学指发生在任何殖民地的任何医学实践,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殖民文化基础的殖民医学在租界及通商口岸城市得到迅速推广。1843年,上海开埠,殖民医学引入沪上,然而殖民医学及其相关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因其殖民性遭到民众的怀疑和抵抗。那么双方冲突主要表现在哪里,原因何在?妥协又是如何达成,动因何在?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本文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华洋两界的视觉冲突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描述到“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相反“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华洋迥异之环境卫生面貌凸显了认识上的巨大差别。
17、18世纪启蒙时代以后,资产阶级形成了身体、环境的新认识,将净化、消毒、杀菌确立为预防疾病的标准生活习惯,都市公共卫生受到重视,卫生管理事业得到积极推动。开埠后,西方殖民者将母国卫生管理体制搬到上海,1862年英格兰人约翰•豪司被任命为公共租界卫生稽查员。大约1 860年,租界开始清除粪便和垃圾的工作,整治乱搭乱建。1897年工部局任命一名专职人员担任卫生处处长,标志着一个现代化公共卫生机构在上海(租界)的开始。由此,租界防疫工作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对公共卫生有着严格细致的管理:界内“逐日另有夫役,沿街打扫龌龊污泥等类,用马车载送郊外,乡民买去肥田”,而且“各家马桶每日倾倒有人,东侧尿沟皆有定所”;加强租界道路的整修,“如界内之地,概用碎石砖填垫,俟人足迹履平则又垫,凡四五次。另用石片石子以千斤铁滚过,用马拖平,必期坚固,遇雨不潦而止,雨后即补填。掘地数尺,接埋水管,以通积水,这些措施有效地预防了疾病的滋生和蔓延。
在华界,人们也知道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只是它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环境卫生相比,范围更小,内容更简单,大概可用“自扫门前雪”来概括,不涉及公众活动场所,故在开埠初,城厢内“溺桶粪坑,列诸路侧,九曲池中水不畅流,且其中掷瓜皮者有之,倒垃圾者有之,以最雅之处易而为龌龊之场。可见当时华界环境之事既无人管理,民众亦缺乏足够认识及重视。“坑间极多,入夏以来,臭气熏人”。“街口狭窄之处,沿街尽是便桶垃圾,任人小便堆积,若无人过而问者。挑粪者则桶不用盖,更觉难堪”。甚至“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对脏乱情景极为漠视。但也有人对此景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如郑观应认为,须“仿照租界章程设局……月收车费、各家灯捐、垃圾捐、各码头捐,以备费用”。还有人提议,“上海洋场经工部局照西国收捐修整洁净,不论大小街道逐日按时打扫,各河浜内不准倾倒龌龊”。又有人批评垃圾满地是因监察不力:“中国保甲非比外国巡捕终日梭行巡缉,以致疲玩成风,置通衢往来之地于度外。”建议当局“严派保甲随时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即予薄罚”。有人则建议:“仿照西人办法,按房按业抽捐,选派公正殷实之人设局总董”,首先清理店铺占有街道,然后“修整街道,浚通水沟东厕尿池,于僻静隙地,酌量分设,派人经营……并多雇夫役,逐日分段挑选龌龊,拣城外空地堆储待售……”
虽然这些认识及建议多仿效西人,体现了人们思想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只是部分人群的认识,或者说它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先知”,并非多数民众之想法。因此在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华人)民众与殖民卫生制度执行者时有冲突发生。
二、卫生检疫制度下的冲突
卫生检疫可谓是冲突最多也是最剧烈的地方。通商口岸开放后,日益发达的海陆交通为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创造了传播机会。1873年,上海租界制定了检疫章程,实施检疫。1894年,鼠疫从海上登陆中国境内。是年6月,上海工部局要求“凡船之由香港、广州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令其停泊下海浦外六里”,并“请西医上船稽查"。同时,工部局在租界积极开展防疫工作。190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西人顾(雇)得工役多名,分往里虹口及西华德路东桂芳里等处逐一稽查,凡有墙壁污秽者,为之粉饰,并用解疫药水洒之”。1909年,食物供应和流通环节规定,“所有不合宜之食物、各水果蔬菜等以及各种气(汽)水等,一概不准摆设市上出卖……倘有用不合卫生之法制作各种气水等,一经查出,即将其制造之器具全行充公……”。1909年,英美工部局为防范鼠疫,要求居民“凡板壁地板等处,如有大小窟窿,一律设法填塞”。天气炎热之季,由于道路不平,低洼积水,易潜生蚊虫,酿成疟疾等疫病流行,1909年,工部局要求界内居民和近界乡户填平道路,积水处洒以消毒杀虫药水。
相对严密的防控措施使鼠疫未对上海造成大的危害。直到1908年,上海首次检出鼠疫。1910年方出现人间鼠疫疫情。从1910年至1924年,上海每年发现的鼠疫病人不过数人或数十人,15年间合计仅100例。
然而租界的制度和管理并没有得到华人的积极支持。从1907年8月15日颁布的《清道示谕》来看,挑粪者似乎并不是很配合管理者的工作,故在违反规定时会受到一定惩戒,具体根据《租界章程》。1910年11月19日,《申报》报道了王安琴等人因与检疫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并受到惩办的事件,同期还追踪报道周毛毛等人与检疫人员冲突事件。可见在卫生防疫的具体实施中,时有分歧甚至冲突发生。分歧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及实践条件不够现实。比如1901年关于水果蔬菜及汽水的管理规定,对于不晓细菌学说,且不能方便获取洁净食物的人群来说还是难以遵守,并且当时食不果腹者不少,只要能吃饱,谁还管它是否干净。更重要的是,实施卫生检疫措施时殖民者的歧视做法和嚣张气焰会让华人的抵制情绪更加激烈。“吴淞口外有‘海关检疫处’,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侮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在食品肉类等检疫上,其检查的主要是售予租界外侨的牛、 羊肉等,而向华人出售的肉类几乎不进行检查。
观念分歧之外,冲突还源于经济上的损失。检疫工作难免有物品的损坏,消毒防疫也会带给被检者财物耗损,为此,租界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安抚居民不满情绪,缓和矛盾。如1910年因查鼠疫,损失衣物,及熏洗房屋,导致各店铺经济损失,租界采用减免租金办法给与补贴。这些举措均有利于卫生检疫工作的推进。但无论如何,检疫制度无法脱离殖民本色,不可能以被殖民者为本,冲突在所难免。
三、用水习惯的分歧
在检疫之外,水源洁净问题也是分歧之一。这一分歧自然离不开上海居民取水用水的固有习惯。开埠前,居民世世代代都直接取用江河溪浜之水或井水,尤其是河浜,而河浜除了供饮用与清洁之用,还需排泄生活污水和垃圾。开埠后,迅速膨胀的人口及急剧扩展的城市规模,使原有的河浜或被填没或受污染,居民用水日益困难,取用河水虽用明矾澄清,仍腥臭难闻。黄浦江是上海最主要的饮用水源,也是上海城区最大的污物排泄处,污染日趋严重,而水的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日惭显著。鉴于此,租界西医生普遍认为,必须对污水进行沉淀、消毒或另作处理,以防痢疾、霍乱、疟疾等病菌滋生,杜绝崩蚀溃疡、腐烂性溃疡、寄生虫发生。改善居民用水提上议事日程。
1872年,《申报》提出“居民所食用之水,每多泥沙而未能清洁……炎天酷暑,外潮之水,黄沙污泥,人口每有成秽之味”,倡议诸商户集资建水池,以净水供各户各铺。次年,松江路6号沙漏水行设制水船一艘,专供清水以民用。1875年,由洋商建成一座小型自来水厂,制造清水出售。1882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建水厂于杨树浦,翌年开始向租界地区供水。1885年,法租界也设自来水厂供商民使用。
初期,使用者极其有限,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心存疑虑,并生出各种谣言。人们传说水有毒质,饮之有害,同时对当时为数较多的水夫的生计造成威胁。自来水公司不得不通过租界当局向上海地方政府求助,为此,当地政府特在《 申报》上刊发申明:谣言“均属不确,现在此处查验,极为清洁。自来水随处可以取携,用之不竭,水清价廉,与从前民间用水,相差极大。地方清洁,食水澄清,居民可免灾疫。同时,强调自来水有利于防止火灾的发生,并劝说水夫另谋其他出路。
十九世纪后期,自来水在租界得到了迅速地推广。自来水的推广,大大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从卫生角度认识到水质与民众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供水系统对城市卫生的重要性。在其带动下,华界邑绅亦倡议仿效。1902年9月,内地自来水厂在高昌乡近郊高昌庙建成并供水。191 1年10月27日,官办闸北水电公司建成供水。
四、病死观的纠结
如果说因为市容建设、卫生检疫及水源洁秽关系到多数人的健康,能对维持地方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殖民医学下的迫切改造不时引发矛盾与冲突,那么病死观作为属于个体认知的一部分,对政局影响不那么直接而突出,殖民医学下的卫生管理及教育也相应呈现得缓和而有选择性,而居民病死观在保持朴素而传统的主要基调下,个别方面显现了冲突与妥协的情形。
l固守传统认知
自古有吴越尚鬼神之说,故每遇疾患,“尚鬼信巫,疾病专事祈祷”,或“俗信鬼神,有疾病先祈祷,而后医药。药无效,辄安之命数”,甚至“送鬼迟则悔咎无穷矣”。虽然仪式治疗中巫觋时常借助药物取得疗效,但并不影响以鬼神为中心的疾病观。1906年一位美国律师在《纽约时报》讲述了一段巫师治病的奇怪故事,某女子患严重的梦呓症,巫师认为其体内藏有狐狸,需施法驱除,即用棍棒猛击患者头部身体,经过多日折磨,没有治愈。终于在一个深夜,邻居听到其惨叫并将其救起,但这位患者反而受到指控。结果,法官没有征求外国陪审的意见直接休庭,患者困境如旧。由此可见,鬼神致病说在华人各阶层均有认同。
同时,居民保持着一些确有疗效的防病习俗:“五月五日端午……以艾和菖蒲、楝枝悬门上,食角黍,饮雄黄酒,争市石首鱼烹……收百草阴干,以备药材……戒坐户栏,云犯之得疰夏症。七月立秋日食瓜,饮新汲水,云可免疟痢”。其中端午节“以艾和菖蒲、楝枝悬门上”“收百草阴干,以备药材”“戒坐户栏”等习俗沿袭至今。即使大肆宣传租界公共卫生新理念的《申报》也登载诸如《急救吊脚痧》《痘疫宜防说》等介绍传统医学防疫方法的文章,说明传统致病、防病观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殖民医学只在政策层面上通行,不多涉足旧有疾病观。
2斗痘接种流行
接种牛痘在内的数种疫苗,不仅能使驻沪白人免受诸多恶疾威胁,而且能彰显近代医学及殖民国政治之优势。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痘接种术熟练地掌握在华人医生手中,西医生操作不易;二是牛痘技术相对简单,有利于推广;故牛痘得以大力推广以巩固(半)殖民统治。尽管之前人们对接种已有认识,但仅限于人痘,对牛痘或其他疫苗接种,颇为陌生,甚至恐惧。这恐惧是对西医的怀疑,对殖民者的排斥。对此,租界利用民众重功利的心理,借助传统医疗文化对人们进行拉拢和说教。如大法国工部局广告称: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人之德也。’该广告在措辞上沿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名称一一大方脉(相当于现在的内科),接种地点则安排在中医诊所,这样一来,华人更容易接受牛痘术。更重要的是,租界还对接种牛痘之贫者相应补贴“三百文”以调养。1872年,公共租界亦赏给牛痘接种成功的儿童每人300文钱,相当于18市斤猪肉的价钱。
虽然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上海地区牛痘接种人数,但从开埠后疫情来分析,在二十三年次的疫情中,天花共有五次,次于霍乱和喉疾(可能是白喉与猩红热),说明天花的爆发的次数及危害相对小,这与牛痘的推广不无关系。之外亦有其他疫苗接种,且人数不少。
3.公墓丧葬扩大
江南素有停柩与土葬风俗。开埠后,上海人口激增,疫病发生频率日益增加,死亡人数相应上升。传统丧葬习惯往往会让疫病尸体再度成为传染源;更糟糕的是,疫病死亡人口中,大多数为贫穷者,家属无力及时落葬。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便会引起疫病(再度)蔓延,尤其是温热时节,尸体腐败快,疫病传播将加剧。因此,19世纪中期始租界大力推行公墓埋葬。然而,接受者无几,并时有冲突发生。最闻名者当为1862年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关于沪上宁波人埋葬的冲突。后来,由于公墓价格相对便宜,落葬花费相应低廉,加上租界的强制推行,选择公墓者逐渐增加,公墓规模日益扩大。1862年到1926年间被市工部局记录备案的就有6处。
五、利益与认知的整合
综上,清末上海地区公共卫生意识冲突时有发生,其范围多为殖民医学实践领域,以市容建设、检疫防疫、水源清洁及接种、丧葬为中心的病死处理为主要内容。
虽然冲突可归结于传统卫生意识与殖民医学及卫生思想的矛盾,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应当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双方做出的妥协正是经济利益的考量和平衡。如卫生检疫工作,倘若没有可观的经济补偿,工作开展谈何容易;自来水的推广亦遭遇价格及挑水工收益的问题;而牛痘与人痘的竞争,虽然人痘在华流行之现实为牛痘推广奠定了重要认知基础,但人们接受牛痘不仅因其操作便捷、技术稳定,免去人痘接种的高昂费用,更重要的是能在接种后得到丰厚奖赏。落葬方式表达了生者对亡者及先人的尊重,对祖训的遵从,而一旦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尤其是牵涉到切身经济利益,旧有观念和传统习俗也可做相应让步,因而催生新的生活方式与理念,这恐怕也是殖民医学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当然,经济利益作为这场冲突发生、发展、结局最外化、最直接的决定者;之上又有更为抽象而深刻的影响因素,那就是移民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埠初期,大量移民进入上海,有外来殖民者,有内地避难者,并以后者居多。殖民国家移民多为上层白人,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新制度最适应者,能成为一定范围内的行为榜样,而内地移民更多地表现为对新环境的适应。尽管新制度强制推行在原住民,甚至内地移民中产生抵制或反抗,但最后也只是形成殖民者政策上的略微调整与民众行为方式改变以配合的结果。
最后,是殖民医学的科学有限性产生妥协。面对半殖民地民众之抵抗,殖民者政策不时表现出怀柔的一面。这既是殖民文化渗透式的战略考虑,又是近代科学本身的有限性所导致的。如在检疫时,海关对于怀疑的行李,仍然采用了华人传统驱疫手段:“熏以硫磺烟”。在鼠疫防控中,认为堵住鼠洞,即可防“疫气”外泄。
因此,殖民医学下的冲突与妥协表明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近代化不彻底。或许有人会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及上海自治运动酝酿了华界卫生管理的不少新思想和新制度,涌现出诸多近代公共卫生思想的倡导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移风易俗卫生运动,人们卫生意识已迈向近代化。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居民卫生观念改进非常有限,辛亥革命前,上海老城厢内依然脏乱不堪,民众依然我行我素。表面而短暂的妥协只能维持短时的井然有序。
一、华洋两界的视觉冲突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描述到“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相反“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华洋迥异之环境卫生面貌凸显了认识上的巨大差别。
17、18世纪启蒙时代以后,资产阶级形成了身体、环境的新认识,将净化、消毒、杀菌确立为预防疾病的标准生活习惯,都市公共卫生受到重视,卫生管理事业得到积极推动。开埠后,西方殖民者将母国卫生管理体制搬到上海,1862年英格兰人约翰•豪司被任命为公共租界卫生稽查员。大约1 860年,租界开始清除粪便和垃圾的工作,整治乱搭乱建。1897年工部局任命一名专职人员担任卫生处处长,标志着一个现代化公共卫生机构在上海(租界)的开始。由此,租界防疫工作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对公共卫生有着严格细致的管理:界内“逐日另有夫役,沿街打扫龌龊污泥等类,用马车载送郊外,乡民买去肥田”,而且“各家马桶每日倾倒有人,东侧尿沟皆有定所”;加强租界道路的整修,“如界内之地,概用碎石砖填垫,俟人足迹履平则又垫,凡四五次。另用石片石子以千斤铁滚过,用马拖平,必期坚固,遇雨不潦而止,雨后即补填。掘地数尺,接埋水管,以通积水,这些措施有效地预防了疾病的滋生和蔓延。
在华界,人们也知道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只是它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环境卫生相比,范围更小,内容更简单,大概可用“自扫门前雪”来概括,不涉及公众活动场所,故在开埠初,城厢内“溺桶粪坑,列诸路侧,九曲池中水不畅流,且其中掷瓜皮者有之,倒垃圾者有之,以最雅之处易而为龌龊之场。可见当时华界环境之事既无人管理,民众亦缺乏足够认识及重视。“坑间极多,入夏以来,臭气熏人”。“街口狭窄之处,沿街尽是便桶垃圾,任人小便堆积,若无人过而问者。挑粪者则桶不用盖,更觉难堪”。甚至“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对脏乱情景极为漠视。但也有人对此景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如郑观应认为,须“仿照租界章程设局……月收车费、各家灯捐、垃圾捐、各码头捐,以备费用”。还有人提议,“上海洋场经工部局照西国收捐修整洁净,不论大小街道逐日按时打扫,各河浜内不准倾倒龌龊”。又有人批评垃圾满地是因监察不力:“中国保甲非比外国巡捕终日梭行巡缉,以致疲玩成风,置通衢往来之地于度外。”建议当局“严派保甲随时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即予薄罚”。有人则建议:“仿照西人办法,按房按业抽捐,选派公正殷实之人设局总董”,首先清理店铺占有街道,然后“修整街道,浚通水沟东厕尿池,于僻静隙地,酌量分设,派人经营……并多雇夫役,逐日分段挑选龌龊,拣城外空地堆储待售……”
虽然这些认识及建议多仿效西人,体现了人们思想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只是部分人群的认识,或者说它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先知”,并非多数民众之想法。因此在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华人)民众与殖民卫生制度执行者时有冲突发生。
二、卫生检疫制度下的冲突
卫生检疫可谓是冲突最多也是最剧烈的地方。通商口岸开放后,日益发达的海陆交通为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创造了传播机会。1873年,上海租界制定了检疫章程,实施检疫。1894年,鼠疫从海上登陆中国境内。是年6月,上海工部局要求“凡船之由香港、广州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令其停泊下海浦外六里”,并“请西医上船稽查"。同时,工部局在租界积极开展防疫工作。190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西人顾(雇)得工役多名,分往里虹口及西华德路东桂芳里等处逐一稽查,凡有墙壁污秽者,为之粉饰,并用解疫药水洒之”。1909年,食物供应和流通环节规定,“所有不合宜之食物、各水果蔬菜等以及各种气(汽)水等,一概不准摆设市上出卖……倘有用不合卫生之法制作各种气水等,一经查出,即将其制造之器具全行充公……”。1909年,英美工部局为防范鼠疫,要求居民“凡板壁地板等处,如有大小窟窿,一律设法填塞”。天气炎热之季,由于道路不平,低洼积水,易潜生蚊虫,酿成疟疾等疫病流行,1909年,工部局要求界内居民和近界乡户填平道路,积水处洒以消毒杀虫药水。
相对严密的防控措施使鼠疫未对上海造成大的危害。直到1908年,上海首次检出鼠疫。1910年方出现人间鼠疫疫情。从1910年至1924年,上海每年发现的鼠疫病人不过数人或数十人,15年间合计仅100例。
然而租界的制度和管理并没有得到华人的积极支持。从1907年8月15日颁布的《清道示谕》来看,挑粪者似乎并不是很配合管理者的工作,故在违反规定时会受到一定惩戒,具体根据《租界章程》。1910年11月19日,《申报》报道了王安琴等人因与检疫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并受到惩办的事件,同期还追踪报道周毛毛等人与检疫人员冲突事件。可见在卫生防疫的具体实施中,时有分歧甚至冲突发生。分歧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及实践条件不够现实。比如1901年关于水果蔬菜及汽水的管理规定,对于不晓细菌学说,且不能方便获取洁净食物的人群来说还是难以遵守,并且当时食不果腹者不少,只要能吃饱,谁还管它是否干净。更重要的是,实施卫生检疫措施时殖民者的歧视做法和嚣张气焰会让华人的抵制情绪更加激烈。“吴淞口外有‘海关检疫处’,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侮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在食品肉类等检疫上,其检查的主要是售予租界外侨的牛、 羊肉等,而向华人出售的肉类几乎不进行检查。
观念分歧之外,冲突还源于经济上的损失。检疫工作难免有物品的损坏,消毒防疫也会带给被检者财物耗损,为此,租界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安抚居民不满情绪,缓和矛盾。如1910年因查鼠疫,损失衣物,及熏洗房屋,导致各店铺经济损失,租界采用减免租金办法给与补贴。这些举措均有利于卫生检疫工作的推进。但无论如何,检疫制度无法脱离殖民本色,不可能以被殖民者为本,冲突在所难免。
三、用水习惯的分歧
在检疫之外,水源洁净问题也是分歧之一。这一分歧自然离不开上海居民取水用水的固有习惯。开埠前,居民世世代代都直接取用江河溪浜之水或井水,尤其是河浜,而河浜除了供饮用与清洁之用,还需排泄生活污水和垃圾。开埠后,迅速膨胀的人口及急剧扩展的城市规模,使原有的河浜或被填没或受污染,居民用水日益困难,取用河水虽用明矾澄清,仍腥臭难闻。黄浦江是上海最主要的饮用水源,也是上海城区最大的污物排泄处,污染日趋严重,而水的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日惭显著。鉴于此,租界西医生普遍认为,必须对污水进行沉淀、消毒或另作处理,以防痢疾、霍乱、疟疾等病菌滋生,杜绝崩蚀溃疡、腐烂性溃疡、寄生虫发生。改善居民用水提上议事日程。
1872年,《申报》提出“居民所食用之水,每多泥沙而未能清洁……炎天酷暑,外潮之水,黄沙污泥,人口每有成秽之味”,倡议诸商户集资建水池,以净水供各户各铺。次年,松江路6号沙漏水行设制水船一艘,专供清水以民用。1875年,由洋商建成一座小型自来水厂,制造清水出售。1882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建水厂于杨树浦,翌年开始向租界地区供水。1885年,法租界也设自来水厂供商民使用。
初期,使用者极其有限,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心存疑虑,并生出各种谣言。人们传说水有毒质,饮之有害,同时对当时为数较多的水夫的生计造成威胁。自来水公司不得不通过租界当局向上海地方政府求助,为此,当地政府特在《 申报》上刊发申明:谣言“均属不确,现在此处查验,极为清洁。自来水随处可以取携,用之不竭,水清价廉,与从前民间用水,相差极大。地方清洁,食水澄清,居民可免灾疫。同时,强调自来水有利于防止火灾的发生,并劝说水夫另谋其他出路。
十九世纪后期,自来水在租界得到了迅速地推广。自来水的推广,大大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从卫生角度认识到水质与民众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供水系统对城市卫生的重要性。在其带动下,华界邑绅亦倡议仿效。1902年9月,内地自来水厂在高昌乡近郊高昌庙建成并供水。191 1年10月27日,官办闸北水电公司建成供水。
四、病死观的纠结
如果说因为市容建设、卫生检疫及水源洁秽关系到多数人的健康,能对维持地方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殖民医学下的迫切改造不时引发矛盾与冲突,那么病死观作为属于个体认知的一部分,对政局影响不那么直接而突出,殖民医学下的卫生管理及教育也相应呈现得缓和而有选择性,而居民病死观在保持朴素而传统的主要基调下,个别方面显现了冲突与妥协的情形。
l固守传统认知
自古有吴越尚鬼神之说,故每遇疾患,“尚鬼信巫,疾病专事祈祷”,或“俗信鬼神,有疾病先祈祷,而后医药。药无效,辄安之命数”,甚至“送鬼迟则悔咎无穷矣”。虽然仪式治疗中巫觋时常借助药物取得疗效,但并不影响以鬼神为中心的疾病观。1906年一位美国律师在《纽约时报》讲述了一段巫师治病的奇怪故事,某女子患严重的梦呓症,巫师认为其体内藏有狐狸,需施法驱除,即用棍棒猛击患者头部身体,经过多日折磨,没有治愈。终于在一个深夜,邻居听到其惨叫并将其救起,但这位患者反而受到指控。结果,法官没有征求外国陪审的意见直接休庭,患者困境如旧。由此可见,鬼神致病说在华人各阶层均有认同。
同时,居民保持着一些确有疗效的防病习俗:“五月五日端午……以艾和菖蒲、楝枝悬门上,食角黍,饮雄黄酒,争市石首鱼烹……收百草阴干,以备药材……戒坐户栏,云犯之得疰夏症。七月立秋日食瓜,饮新汲水,云可免疟痢”。其中端午节“以艾和菖蒲、楝枝悬门上”“收百草阴干,以备药材”“戒坐户栏”等习俗沿袭至今。即使大肆宣传租界公共卫生新理念的《申报》也登载诸如《急救吊脚痧》《痘疫宜防说》等介绍传统医学防疫方法的文章,说明传统致病、防病观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殖民医学只在政策层面上通行,不多涉足旧有疾病观。
2斗痘接种流行
接种牛痘在内的数种疫苗,不仅能使驻沪白人免受诸多恶疾威胁,而且能彰显近代医学及殖民国政治之优势。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痘接种术熟练地掌握在华人医生手中,西医生操作不易;二是牛痘技术相对简单,有利于推广;故牛痘得以大力推广以巩固(半)殖民统治。尽管之前人们对接种已有认识,但仅限于人痘,对牛痘或其他疫苗接种,颇为陌生,甚至恐惧。这恐惧是对西医的怀疑,对殖民者的排斥。对此,租界利用民众重功利的心理,借助传统医疗文化对人们进行拉拢和说教。如大法国工部局广告称: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人之德也。’该广告在措辞上沿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名称一一大方脉(相当于现在的内科),接种地点则安排在中医诊所,这样一来,华人更容易接受牛痘术。更重要的是,租界还对接种牛痘之贫者相应补贴“三百文”以调养。1872年,公共租界亦赏给牛痘接种成功的儿童每人300文钱,相当于18市斤猪肉的价钱。
虽然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上海地区牛痘接种人数,但从开埠后疫情来分析,在二十三年次的疫情中,天花共有五次,次于霍乱和喉疾(可能是白喉与猩红热),说明天花的爆发的次数及危害相对小,这与牛痘的推广不无关系。之外亦有其他疫苗接种,且人数不少。
3.公墓丧葬扩大
江南素有停柩与土葬风俗。开埠后,上海人口激增,疫病发生频率日益增加,死亡人数相应上升。传统丧葬习惯往往会让疫病尸体再度成为传染源;更糟糕的是,疫病死亡人口中,大多数为贫穷者,家属无力及时落葬。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便会引起疫病(再度)蔓延,尤其是温热时节,尸体腐败快,疫病传播将加剧。因此,19世纪中期始租界大力推行公墓埋葬。然而,接受者无几,并时有冲突发生。最闻名者当为1862年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关于沪上宁波人埋葬的冲突。后来,由于公墓价格相对便宜,落葬花费相应低廉,加上租界的强制推行,选择公墓者逐渐增加,公墓规模日益扩大。1862年到1926年间被市工部局记录备案的就有6处。
五、利益与认知的整合
综上,清末上海地区公共卫生意识冲突时有发生,其范围多为殖民医学实践领域,以市容建设、检疫防疫、水源清洁及接种、丧葬为中心的病死处理为主要内容。
虽然冲突可归结于传统卫生意识与殖民医学及卫生思想的矛盾,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应当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双方做出的妥协正是经济利益的考量和平衡。如卫生检疫工作,倘若没有可观的经济补偿,工作开展谈何容易;自来水的推广亦遭遇价格及挑水工收益的问题;而牛痘与人痘的竞争,虽然人痘在华流行之现实为牛痘推广奠定了重要认知基础,但人们接受牛痘不仅因其操作便捷、技术稳定,免去人痘接种的高昂费用,更重要的是能在接种后得到丰厚奖赏。落葬方式表达了生者对亡者及先人的尊重,对祖训的遵从,而一旦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尤其是牵涉到切身经济利益,旧有观念和传统习俗也可做相应让步,因而催生新的生活方式与理念,这恐怕也是殖民医学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当然,经济利益作为这场冲突发生、发展、结局最外化、最直接的决定者;之上又有更为抽象而深刻的影响因素,那就是移民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埠初期,大量移民进入上海,有外来殖民者,有内地避难者,并以后者居多。殖民国家移民多为上层白人,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新制度最适应者,能成为一定范围内的行为榜样,而内地移民更多地表现为对新环境的适应。尽管新制度强制推行在原住民,甚至内地移民中产生抵制或反抗,但最后也只是形成殖民者政策上的略微调整与民众行为方式改变以配合的结果。
最后,是殖民医学的科学有限性产生妥协。面对半殖民地民众之抵抗,殖民者政策不时表现出怀柔的一面。这既是殖民文化渗透式的战略考虑,又是近代科学本身的有限性所导致的。如在检疫时,海关对于怀疑的行李,仍然采用了华人传统驱疫手段:“熏以硫磺烟”。在鼠疫防控中,认为堵住鼠洞,即可防“疫气”外泄。
因此,殖民医学下的冲突与妥协表明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近代化不彻底。或许有人会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及上海自治运动酝酿了华界卫生管理的不少新思想和新制度,涌现出诸多近代公共卫生思想的倡导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移风易俗卫生运动,人们卫生意识已迈向近代化。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居民卫生观念改进非常有限,辛亥革命前,上海老城厢内依然脏乱不堪,民众依然我行我素。表面而短暂的妥协只能维持短时的井然有序。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